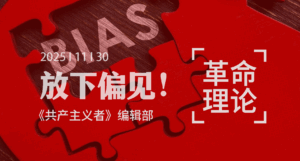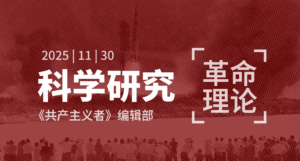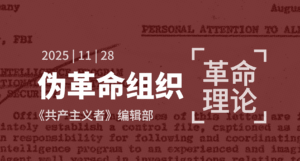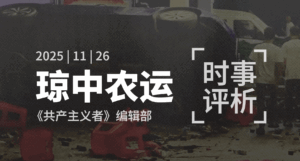目录:
(一)“紧追穷寇”还是马拉松
(二)演绎式与公式化批判
(三)谁在扼杀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
(一)“紧追穷寇”还是马拉松
一周前,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又一次被批判了。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后文简称为“马列毛大群”、“大群”)在自己的“千钧棒:炮打机会主义专辑”中在一周内发布了上百篇批判我们的骂战短文。就如同共革阵曾经遭受到的各方批判一样,我们又一次被套上了好几顶虚无的帽子:讲理论,所以我们叫“书呆子”、“西马派”、“学理主义”;讲实践,我们叫“佳士路线”、“改良主义”、“工联主义”;组织建党,我们叫“南湖划船”、“小资沙龙”;进行宣发,我们叫“唯影响力”、“宣传主义”……一会说我们“投降派”,是中国的合作者,一会我们转身变成了“暴力冲塔”、葬送青年的莽夫,“太暴力”。当有人提问说共革阵到底是什么,他们就会含糊其辞地抛出什么“大杂烩”、“‘白骨精’”、“‘四不像’”、“黑熊精”、“混合黑暗料理”、“魔法学院”、“现代赵括”或“弗兰肯斯坦”之类的抽象概念,把政治上的批判降格为了纯粹的丑化。
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甚至回答不了“共革阵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他们说我们“在英国街头贴宣传海报” ,估计是看了我们《海外支部的首批宣传 —— 来自某英语国家》的帖子后做的猜想。其实他们如果能花个两三分钟查证下图片中出现的几个英文字母就能发现其张贴地点在美国,而非什么“英国街头”。这个错误的出现证明了要么“英语国家”这四个字是大群写手们阅读量的极限,要么是他们的世界观还停留在1776年7月4号的美国独立之前。这样的问题都在至少两篇骂战文中出现,可见其查证事实的能力如何。对于一群连英国和美国都分不清的写手们,我们相信其政治写作水平和其地理水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在“紧追穷寇”的100余篇文章中,马列毛大群说的非常头头是道,说他们“一直忠实宣传列宁同志的政治报路线,同时也维护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并且号召革命者们“把全部的政治生命投入到真正有益于革命的全国政治报路线中去!”。应该都让同志们听听,大群的这些批评家说的有多么准确。这些批评家们讨伐着一切新兴的左派组织,“洞悉一切般”地知晓了共革阵“没有集中”、“没有政治报路线”,对我们组织的了解程度“奇迹般地”超过了组织的成员们。那么我们也想要去问问大群到底是怎样精彩地在内部执行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我们还想问问马列毛大群所向其读者、群聊参与者许诺了几年的那个由“全国政治报路线”建设起来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到底在哪里,而一个全国的、革命的列宁式政党又被他们通过“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建设到哪个行星上去了?
可见,大群的这些写手们、编辑们、纸上谈兵的革命家们到底是把“全部的政治生命”投身到了“全国政治报路线”中还是花在了上述列举的各顶帽子和丑化之词的臆造上,答案被他们自己彻底地揭露了出来。
马列毛大群在批判我们的时候还写道:“唉,还能说什么呢?‘共革阵’都这样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呢?他们已经彻底无可救药,我们再劝就不礼貌了”且我们不过就是“老调重弹”,不惧什么威胁。千真万确,所以他们在一周多内一连发了100篇短文来反复地、“不礼貌”地一劝再劝好让我们不去“毒害革命新芽”,这份诚意共革阵全体都心领了。
这让我们想到了列宁曾写下的一段极具讽刺的评论:“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弗·列宁 《列宁全集》第18卷)。正如如今来自大群的骂战一样,虽然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编辑们反复地说共革阵已经被他们击的粉碎,但他们还是不断地“棒打”、“炮打”、“揭开”、“炮轰”、“戳穿”我们并把“紧追穷寇”变成了一场100篇杂文的马拉松,试图用不顾质量的数量打败共革阵的同志们。
接下来,就让我们仔细看看他们这100篇到底做了什么漏洞百出的攻击。
(二)演绎式与公式化批判
关于民主集中制与支部
在百篇骂战文中,马列毛大群反复攻击共革阵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态度,主要总结下来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泛民主”而没有集中,因此我们是在“反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大群的写手们已经越过了我们的文章内容,“奇迹般地”了解到我们组织内部“没有集中”,这些从未加入过我们组织的人竟然能够靠演绎的模式推理出这一项指控可见其想象力之强。
其次,大群指控我们的文章《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回避了集中环节的必要性,只要民主环节”并“空谈民主,反对集中”,且还判断“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尚且年幼的阶段放任自觉性不足的基层组员掌握过多的民主权力,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也就成了必然”。我们不禁思考,民主二字到底激起了大群怎样的恐惧,使其只要看到共革阵提到组织内的民主环节就吓得发抖,胡乱地指控说共革阵“反对集中”、纵容“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一文中解答了,不过只会断章取义地进行公式化批判的大群写手们似乎碰巧没有引用上。在文章的第一段就提到了一个革命组织所要追求的便是能对抗和超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织行动的严谨程度、迅速程度、集中程度”;在关于如何落实民主集中制上,我们也做了相对应的表述:
“这里必须强调,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抽象原则,它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组织架构中。革命党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层级。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它由全党选举产生,代表全党的意志。中央委员会再从自身成员中选举产生政治局,负责处理重大决策。政治局之下设有书记处,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日常的组织事务,而不是代替政治局做出战略决策。换句话说,政治局必须主导决策,因为它代表的是全党的集体意志,能够高效而统一地制定政策。如果让书记处主导决策,权力就会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削弱党内的民主讨论和集体智慧,导致决策偏离全党利益,破坏党的团结和效能……真正的党内民主,是在充分讨论、允许少数派坚持意见的前提下,最终形成全体一致的行动。这样的统一不是表面的,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和对历史方向的共同认同之上。 ”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共革阵被指控的“反对集中”和纵容“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这两项罪名被彻底地颠覆了。共革阵不“反对集中”,而是强调“集中程度”的重要性和建立“明确的领导层级”的必要性;共革阵不纵容“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而是强调一切观点与意见都在经受过“充分讨论”的检验后、政治局的决策主导下才会被付诸行动。同时,我们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列宁式政党下对党员纪律的要求“只有那些在日常工作中承担责任、贡献劳动的成员,才配得上享有党内的权利[即组织内的各项民主权利]。相反,那些只挂名、不参与、不履行义务的人,就不能成为党的成员 ”与民主集中制的参与者。而这样的要求与方针竟被大群理解为了“小资产阶级的泛民主”和“放任自觉性不足的基层组员”,看来其对党员身份和民主权力的持有者也有较大的理解偏差。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践是以秒为单位在组织内进行的,共革阵的组织建设保证了投票选举等民主权力和集中的组织架构之同时存在,让组织主张的“自由讨论、一致行动”从来不是什么空谈。
当然,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刻意地忽略掉了上述引文,觉得但凡一篇文章谈论民主,那就是“反对集中”,这一点我们从他们庸俗的理解中可以看的相当明白。在一篇骂战文中,大群提到:“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而大群对上下级关系的解释则是“下级往往存在着多数的自发同志,自觉同志只占少数,而上级代表着少数掌握着专政权的自觉同志”。这就是大群眼中的民主集中制: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运行模式,对上下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中央是如何从全党诞生的等话题便避而不谈。与我们的文章《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中提到的具体党建策略不同,大群不会回答他们眼中“列宁和毛主席一生坚持贯彻的民主集中制”里到底有什么机构、有什么程序来产生所谓的上级与中央,由此可见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上下级关系和组织内的中央是一贯存在、雷打不动且不允许质疑的,而其形成的成因更像是一种论资排辈而非明确的选举和任免程序。
如上文所述,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一看到民主二字就吓得哆嗦,实际上害怕的就是自己在有实际程序和“领导层级”的民主集中制下失去自己的位子。落到实处,他们害怕的到底是“充分讨论”、“选举产生”、“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还是民主集中制的一切细则,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最明白。
断章取义地引用只是他们骂战策略的一部分。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拉起了一套转换公式来把共革阵的理论转化成他们能够批判的对象。就如同我们先前分析的那样,我们写下的“一旦决议形成,全党统一行动”变成了 “一昧地实行全民民主,搞公投”、我们主张的“革命党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层级”则被他们理解为了“避而不谈或者说刻意贬低集中制”。这种骂战的演绎化和公式化是由绝对的恐惧造成的,他们连直接批驳我们的理论都不敢做,得把共革阵的理论在一次次的替换、扭曲与罗织后才敢回复,还必须把引用我们的原文都画上删除线以防止直视。我们承认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和编辑们都是辛苦的,为了批判我们组织的路线,其必须研发出一条新的路线以便自己先射箭后画靶地搞骂战。
这一点从他们对我们党支部模式的攻击中清晰可见。我们在《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一文中表明“我们并非一个网站、讨论区、频道或者群组,而是立足于党支部、书记制、代表大会、政治委员会等民主集中制传统的政治组织”和“党支部是我们真正的主力,和我们的重心,一定不能把领导层这个中心当成重心来看,导致政治完全包办、基层的同志们只是旁观者而非党实际工作的承担者”。大群批判说“革命党必然是以党中央为重心,党支部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共革阵鼓吹党支部是主力、是中心,无非就是向其他泛左翼组织许诺权力分享,方便更好的联合泛左翼组织,搞南湖划船路线罢了”。我们说的党支部是“重心”一转眼就被大群改写成了“中心”,而我们说的“领导层这个中心”则又一次地在大群的批判中神奇消失了。党支部之所以是“重心”是因为其作为现实革命运动的前线和革命组织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而存在,并非是大群臆想的“向其他泛左翼组织许诺权力分享”等动机。关于这一指控我们不妨也做下戏谑的翻译:
“脊椎动物(革命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细胞(党支部),所以这是说智人(共革阵)要走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甚至是单细胞生物的反革命道路,是要反转数亿年的进化,回到阿米巴原虫和草履虫的时代。”
关于共革阵的指导思想
大群的几位写手是如此理解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将毛主席、托洛斯基(左倾)、葛兰西(改良)这三个风马牛不相及,有着重大分歧的人的思想视为指导思想”、“混合了托洛茨基、葛兰西、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毛泽东、托洛茨基、葛兰西一并挂在墙上”。还有一位甚至写道“笔者初次尝试总结共革阵思想时,便遭到了其惊吓”,因此将我们定性为“弗兰肯斯坦”。这位写手,请你冷静些、安静些,让我们好好看看这个让其遭到惊吓的“指导思想”的迷思。
其实问题的本质是无比简单的:马列毛大群的那套转换公式又开始作祟了,即我们写了三篇“思想评析”他们就将其当作了共革阵的“指导思想”。这个写作思想评析=当作指导思想中的逻辑断层实在是令人费解,评析只是一个中性的动词或文章类型,就像马克思评析过黑格尔、列宁评析过考茨基一样,难道在大群的写手眼中马克思将黑格尔作为了其指导思想?列宁将考茨基“挂在墙上”?
没错,共革阵曾写作了对毛泽东、葛兰西和托洛茨基的思想评析,但我们明确地表明了思想评析的目的与意义。在《葛兰西思想评析》一文中我们提到:“本文旨在简述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如对知识分子的深入解释、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与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常识’、霸权装置(即精神生产资料)与‘整体国家’的关系。 ”;在《逝世49周年–毛泽东思想评析》一文中我们提到“我们重新讨论这位革命者遗产的指导性意义以及局限,他的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现实意义。 ”;在《八十五年之际–托洛茨基思想评析》一文中我们写道:“[本文]整理了托洛茨基重要的革命思想,以扩充今日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宝库,推进我们有生之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请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好好看看,以及请那位被“惊吓”到的写手仔细读读,这三篇思想评析中究竟是有哪篇讲了诸如“某某人的思想就是共革阵的指导思想”之类的话?
关于共革阵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中写的相当明了了:“很简单,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是革命派”。而至于我们对过去革命者的态度也有着重解答:
“我们从来就不是“某人之派”。我们对任何历史中革命者的看法都不是要“百分之四十九好百分之五十一坏就是坏,百分之四十九坏百分之五十一好就是好”这种僵硬的立场,我们拒绝将历史人物归为两大类,所谓“坏人”和“好人”,将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归为“可读”和“读了脏眼睛”的……我们坚持就事论事,不以主观对任何人的看法出发去分析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任何革命者的名字都单单不足以真正表达我们的思想。”
这也是我们写作思想评析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后续还会继续写作其他革命者们的思想评析,请大群的写手们不要再将其错当为任何指导思想的宣言,也请那位“遭受了其惊吓”的写手不要又吓破了胆。
论革命条件、群众斗争与党的形成
大群的写手们在批评我们所谓“歪曲列宁主义”时,反复批评我们强调群众斗争、从改良实践到革命斗争的逐步演化和阶级意识生成的辩证过程是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甚至将我们视作是纳杰日丁式的“旧社会民主党人的遗产”。显然,这些写手们误解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与列宁都并不永恒地活在1902年或是2025年,任何革命路线都必须依据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与阶级结构来建构。列宁主义从来不是一套可以脱离具体斗争环境而机械套用的路线公式。恰恰相反,它的核心精神就在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策略,把握阶级运动的客观节奏。
1902年《怎么办?》一文中,列宁开创性地强调了职业革命家、集中领导以及全国性政治报的作用。这篇文章是在一个高度压制、工人运动尚处在经济主义阶段的俄国写成的。在那时,俄国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能够承载政治斗争的组织形态,社会主义者被迫以小圈子活动为主,革命工作主要集中在秘密组织与宣传鼓动之间。列宁在这一阶段强调政治报,不是因为他认为组织可以仅靠文字构成,而是因为在高度压制之下,政治报是联系分散地区、统一思想方向、培育组织骨干的唯一可能形式——这是一切共产主义革命者都认同的基本纲领。
马列毛大群对我们的攻击集中在了这一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列宁对于政治报在‘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这一进程中所占据的关键地位的论断,但是我们同样也没有忘记列宁在做出这个论断前同时肯定的说法,即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有办得极好的全国性政治报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句话让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兴奋了,他们觉得自己抓到了我们的命门并能证明共革阵“就是一百年前机会主义者纳杰日丁的徒子徒孙 ”。让我们再仔细地看看《怎么办?》的原文吧,列宁写道“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有办得极好的全俄报纸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完全正确。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 ”大群的写手们忽略掉的便是这句话背后的辩证关系:全国的政治报是“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唯一方法,但政治报本身也需要一定规模的政治组织来负责发行与传播。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能找到一个可以与《火星报》的规模和管理模式相对应的组织吗?当列宁在1902年写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时,其要走向是1905年和1917年的起义与武装革命,而列宁当时具有的基础条件,即《火星报》本身和各有利势头在现在的中国还仍在襁褓。让我们看看《火星报》在1900年8月发表的《编辑部的话》是如何描述当时的革命形势的:
“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近几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知识界传播之快,是异常惊人的,而与这一社会思潮相呼应的却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独立产生的运动。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向往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地方性的鼓动小报广为流传,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报供不应求,政府变本加厉的迫害已阻挡不住这个运动了。监狱中拥挤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满之患,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听到俄国各地有人被“抓获”、交通联络站被侦破、书报被没收、印刷所被封闭的消息,但是运动在继续发展,并且席卷了更加广大的地区,它日益深入工人阶级,愈来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俄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进程、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将保证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最终冲破重重障碍而向前发展。 ”
共革阵要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革命情形与1900年的俄国相较不远但并不代表其完全重合。而我们在21世纪20年代所强调的“政治组织”正是一个有能力撰写刊物、制作刊物、传播刊物的《火星报》式组织且在各地区拥有自己的党支部和组织化存在。若是没有这些准备,自发的无产阶级又怎么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并在革命的理论下组织起来?我们不是马列毛大群所谴责的“反对全国政治报路线”,而是实际地在贯彻政治报路线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革命者在当时的困境是“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因此需要全俄的政治报来辅佐组织建设,而我们目前的窘境不只是没有脚手架,而是连“次木料”都不足够。
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能自信地批判正在为全国政治报做着必要准备的共革阵,也许其觉得自己的“全国网络大群聊”已经足够成熟与完备来执行“全国政治报路线”了、觉得自己的文章已经能够成功传到几亿劳动者手中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他们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时间来写百篇骂战文以镇压我们的不同声音了。所以说共革阵的声音置于马列毛大群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在他们沉浸在自己幻想的甜美中时,我们挑明了他们连包砂糖都没有的现实。
在讨论过政治报路线之后,我们还想补充分析下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密室组织”的关系。当今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愈发庞大,但因为曾经发生过的溃败,其在组织上是原子化的,他们的斗争极度分散,政治表达空间被高强度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密室组织独走”的路线看似能够重建起列宁在那时的某种政治原则,但却是跳过了整个现实的组织难题,用意志代替结构,把手段当作目标。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阶级意识的羸弱和工人没有组织斗争、积累经验、形成稳定团结办法的条件。就算是在列宁那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工人阶级仅仅发动极其有限斗争的年代中,他也从未否定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他只是指出,不能把经济斗争看作最终目的,不能把它作为革命的替代物。列宁明确、直接地将经济斗争视为工人阶级政治成长的“训练场”。难道一个没有在罢工的生产现场经历过组织锤炼的工人,能够在革命的暴力斗争中承担组织任务?一个地下革命组织正应该做的是在基层运动中保持存在,用党的基层组织机关控制与接管由改良主义发展出的自发经济斗争,并将其转化为政治斗争。就像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及的“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那就只有在现场进行,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
显然,我们的路线从来不是将改良斗争作为终点,而是将其视为必要起点,这是我们中国革命者重建我们的进攻性武器——阶级斗争的唯一方法。在当前条件下,我们既不是要幻想一个就算是1917年都从未出现的“地下红军”,也不是要畏畏缩缩、躲藏在所谓“高度集中封闭的政治报”幌子背后,而是必须建立能够通向那一阶段的现实道路,这才正是列宁思想的真正精髓。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扭曲群众斗争的辩证过程,将革命组织建构异化为与群众运动相分离、甚至凌驾于群众斗争之上的的“先验工程”的任何恶毒思想。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吗? ”,而许多写手们似乎只看到了“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这一部分,因此决定要将自己置于实际革命运动的千里之外,而碰巧忽略了自己应当参与到运动之中、将“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这一标粗的部分。
没有群众斗争的土壤、没有同群众接触的动力,任何先锋队都只是空中楼阁;同样的,没有有着革命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党,群众的自发斗争也不会达到更高的阶段。
那么,革命组织到底是不是从密室中创造出来的?它的最核心、最重要、尽到在革命早期最迫切的产出理论、建立政党基础任务的政治报当然是一个“密室”,但是我们难道要学习中国政府,说着“共产主义永远在路上,社会主义要过渡一百年”?难道我们的革命同群众的有机结合也要等《布站》的老先生们花上一百一千年时间把每一个群众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地下基层组织支持者”?政党是在群众斗争与社会矛盾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在幻想与白日梦中化形的。这才是我们所理解的列宁主义——也是我们面对今天中国现实的回应。
(三)谁在扼杀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
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马列毛大群所展现的除了幽默与低质量的内容外,还体现了目前中国左派政治中的家长式霸权。无人会否认的是马列毛大群是全国线上参与者最多的左派群聊,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其数年的运营使得其领导层积累了相当多的网络政治资源:2万参与者、持续运营的发文网站“布站”和随时可被动员起来愤怒地写下百篇骂战文的写手们。许多新加入政治工作的同志们也许会在大群的规模前产生动摇,认为其群聊的参与人数证明了其政治路线的部分正确。当然,若是规模决定了政治路线的正确,那拥有1亿多党员的现代中国共产党想必也是绝对的“伟大、光荣、正确”。
这样的现实是可怕且需要被推翻的,任何新兴的左派组织若是不服管理、不服从马列毛大群既有的一套“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就会遭受骂战的轰炸。马列毛大群反复地尝试揭示我们的本质,把他们自己对维系家长式霸权的狂热揭露了出来。在大群的眼中,所有的左派组织或多或少、或新或旧地都和自己有着关系,因此包括共革阵在内的左派组织的一切理论产出、政治行动和斗争都不是对革命的贡献而是对他们的反叛与挑战,所以他们需要“棒打”、“炮打”、“揭开”、“炮轰”、“戳穿”一切与其“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相左的左派组织。从这样的标准再看这百篇檄文,大群无疑是成功的,大群的写手与编辑成功地让共革阵的同志们从建设列宁式革命组织的工作中抽离了部分精力、成功地减缓了对其霸权的挑战、成功地展现了自己“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的淫威。可见,在阻塞革命运动这一方面,马列毛大群又一次大获全胜。我们都不用猜想这背后的直接受益者到底是谁了,我们也无意如同马列毛大群一样去散播什么阴谋论,我们仅叙述事实:这种左派内的骂战最为受益的永远是追求“稳定高于一切”的统治阶级,即现代中共政权。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各战线中工作和学习的同志们、本频道的读者同志们、各仍在观望态势的新兴左派组织们,是时候向这样霸权式的“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说不了。我们将不再接受一个毫无组织性与实际工作的、为骂战而生的团体盘踞着话语权;我们将不再接受一批只会复读理论却连其精髓都未曾把握的团体利用其积累起的政治资源打击异见;我们将不再接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被这样的团体代言与绑架,最终走向僵化和溃烂。
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们,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