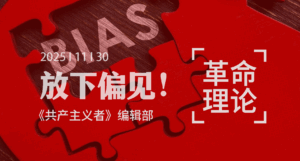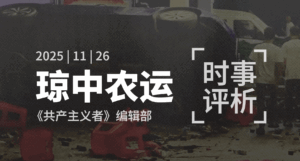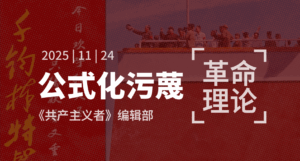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一种奇妙的现象:“黄色”、擦边的性暗示内容越来越多,新生儿却越来越少。人口问题已然成为中国面对的严重问题,雪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2024年出生人口约为954万,虽然相比23年略有回升,但生育率(孕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个数)只余1.08。“龙宝宝”不能掩盖生育数据“赶韩超日”的事实,专家们为了提高生育率想破了头,最终出手了一项大措施:颁布《育儿补贴政策实施办法》。
多还是少?
但是,这个政策的实际内容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支持者说,它是中国近来罕见的全国实施、中央层面管理、一视同仁的政策,并且迎合了经济界“直接发钱”的呼吁,感谢国家都来不及;批评者一看,每孩每年3600元,只发放到三周岁为止,每月300元连奶粉钱都不够,便发出戏谑的哂笑。支持者见状,立刻跳脚:有就不错了,你怎么这么不知感恩呢?又不是你生孩子,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呢?这笔钱,对于那些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可是很有用的!
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共计1.08万元的育儿补贴,究竟算不算多呢?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中国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即便是农村,养育成本平均也有36.5万元,城镇的养育成本平均更是高达66.7万元。收入最低的20%家庭,平均养育成本也有12.6万元,中等偏下的20%家庭则达到了28.2万元,中等的20%家庭。如果到本科毕业,养育成本平均更是达到68万元。即使取最低的数据,育儿补贴所提供的仍不足养育成本的十分之一;相较于平均养育成本,这笔钱也仅在2%左右。难怪会有人形容这笔补贴是“劳斯莱斯五元代金券”。
羊毛出在羊身上
也有人说,这次代金券不过是个开头,往后中共肯定会大发慈悲,继续增加补贴的。然而,这真的是中共的“开恩”吗?这真的是所谓的“补贴”,是中共发给人民的、工资之外的“福利”吗?不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深入的了解,就不能理解它实际的奥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讨论过劳动力的价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再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
也就是说,本来工资中就应当包含让无产阶级能够正常生儿育女的部分,更何况合适的生育率应当为2.1。让我们来算个帐: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城镇一孩0-17岁平均养育成本为66.7万元,二孩则为52.6万元,平均分配到父母2人40年的工作中,每年应有约1.5万元的盈余作为生育的部分。假使我们要求他们省吃俭用一些,将这个费用降至一万,对于一个月薪五千的工人来说,这也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更何况仍有大量月薪远不及此的人呢?
人们都知道,年轻人不肯生娃,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考虑到经济负担难以承受,以致于生育率如此低下。这说明,他们的工资本就不足以覆盖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如今的育儿补贴,借口“发达国家育儿补贴在人均GDP的2.4%到7.2%”之间,只发送了杯水车薪的量。不仅是个人层面,宏观层面,中共拿出的九百亿元相较于其为了“提振消费信心”动辄豪掷万亿的气魄也显得颇为小气。用这点残羹剩饭就想打发无产者“服服帖帖生孩子”,就做他的大头梦去吧!
中国百年人口问题纵览
中国的人口问题为何会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和平年代一年的新生儿数量都比不上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的新生儿数量呢?这需要我们对中国百年来的人口数量进行一个大致的分析。
近代,虽然中国经济崩溃、战火连天,人口死亡率高,但是高生育率弥补了这一点。灾难不断地消耗着超出中国当时生产力能够供给的人口数量,半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吸引了多余的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秩序,不至于让小农经济的瓦解带动着整个社会的崩溃,因此,近代中国的人口大约一直维持在4亿-5亿之间。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社会秩序完全稳定,生产力也快速提升,能够容纳的人口数量快速攀升;多生的观念依旧存在,再加上医疗水平改善,新生儿夭折率大大降低,结果新中国人口数量急速增加。虽然曾有人主张限制人口数量,但并未实行。
直到1970年,中国大约有了八亿人口,人口压力迫使中国通过各种手段,如避孕技术与提倡晚婚晚孕等一定程度上控制人口的增加。新生儿数量有所减少,但人口基数依旧庞大,因此新生儿数量仍能够维持在1700万以上。在这个时候,庞大的人口实际上还是一个负担,因为尚不是特别发达的工业体系并不能消化如此大量的劳动力,多余的人只能呆在农村种地,而过多的农业人口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并无多大的助益。
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由于60年代大量的新生儿在这个阶段进入适宜生育的年龄,十分严格的计划生育措施并未能在短期内快速降低新生儿的数量,但是确实降低了生育率。这给改革开放、拥抱资本、拥抱市场、拥抱世界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工业规模迅速扩张,需求是不用担心的,自有外国承担;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方针下,外国也可以暂且弥补中国工厂机器不足的问题。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劳动力,而历史的机缘给了中国一个数亿级别的人口红利:极为大量的劳动力,简朴的生活与激烈的竞争使得这些劳动力十分廉价;他们的老一辈奉行多生,因此人数较少;他们的下一辈因为计划生育,人数也较少。较低的抚养比从另一个层面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尽情地吮吸着剩余价值汇聚成的大海;官僚砸着超生者的房子,因为这种行为的泛滥会带来工资的提高;高校也在不断扩招,以培养这个世界工厂所需的高端人才。那是一个疯狂而狂飙突进的年代,人口众多是中国最为骄傲的优势。
但是,红利背后已经暗中标明了代价。大批劳动力步入中年,新生儿的数量却因为计划生育的继续实行降得更低,一度跌到1500万左右。经济危机的冲击也为人们泼了一桶冷水,因为劳动力市场逐渐消耗不了那么多劳动力了: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不断有劳动者被抛入失业者的行列;中美蜜月期的结束,可能带来海外市场的缩水;高校扩招,使得一方面学历贬值,另一方面过去的劳动力被投放到了现在,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压力;随着抚养比的增大,工资也必须以某种形式提升。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人口问题势必拖垮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未来某一场大型经济危机的诱因。
于是,2016年,双孩政策开放了,很快又开放到三孩。可是,新生儿数量并没有像中共预想的那样回升,反而一年接一年上百万地减少,直到2022年跌破一千万人。人口红利带来了另一个诅咒:三十年来疯狂的压迫与剥削,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增长,还极大地消磨掉了劳动者的精神。阶层迅速地固化,除了让官僚与资本家的子女高枕无忧,还打消了无产阶级进一步阶级跃迁的愿望。连续几十年的剧烈变化培养出来的强烈的名利意识与愈发黑暗的现实对冲,创造出了这样的一代人:无论对国家的未来相信与否,都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勤劳致富的戒律告诉他们:不劳动者不得食,可是,即使劳动了,也不一定得食。他们不想当牛马,可他们除了牛马就没有可以扮演的角色了;他们想组建家庭,可光是价钱就能让他们望洋兴叹。亲眼看过“奋斗成功”的老一辈却还在絮絮叨叨什么“苦心人,天不负”,讲着“结婚生子”。这种观念的冲突带来了代际的矛盾,使得年轻人的一部分不得不连家庭的观念都抛弃掉。他们自己生存下来已属不易,又怎么会想着人生价值的实现,又怎么会想着生命的延续呢?
于是他们躺平了。他们不再想着要孩子,甚至连新的家庭都不一定要,先保证自己确实能过得好一点吧。这时,资本家们便来了,指指点点地说,你为什么不生孩子?抚养比不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了。他们在盘算,没人生孩子了,谁来打螺丝,谁来送外卖呢?谁来继续给我们提供剩余价值呢?没人生孩子了,养老金岂不是要我自掏腰包?没人生孩子了,我们跟谁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呢?于是,他们便来千方百计地劝年轻人生孩子。在他们那里,生孩子全然不是生命的延续,而不过是剩余价值的延续,是牛马的延续。年轻人不生孩子,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消极抵抗的一种形式,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挑战资本主义剥削的体系。这是另一个层面的罢工。
如何应对?
有一种可谓搞笑的应对方式:有人说,现在正是生孩子的好时机,因为当他们长大时,人口锐减,到处都是无人继承的社会资源,那么无论孩子素质如何,将来都会有不少的社会资源。但是确实也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现在出生的孩子,由于同龄人少,将来会面临更少的竞争。
这种观点可谓大错特错,因为中国人内卷的主要原因,绝非人口太多,而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结构性矛盾。在这种观点中,似乎失业仅仅是因为劳动力人数多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偶然的组合。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总是在提升科技、改良工具,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同样的需求就会用更少的劳动力满足。多余的劳动力便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可以随时保有一支失业大军,以确保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竞争关系,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压低工资。即使在几十年后,人口数量锐减,看似提供的劳动力少了,可是需求也降低了,再加上届时AI的应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仍旧会存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
因此,脱离这种内卷状态的方法,从来不在于规定人数多少,而在于打破这个不断创造出匮乏、内卷与贫穷的体制,我们不仅要自己掌握自己创造的财富,更要接管整个世界,让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能,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只有这样,生育才会真正成为个人延续生命的选择,而不是被政策、意识形态或经济条件裹挟的被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