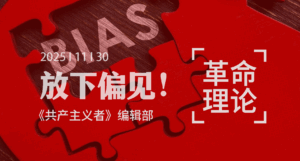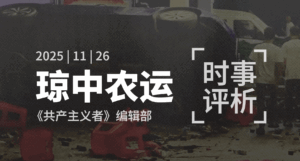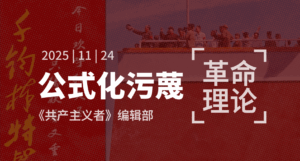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尘埃落定了。高考结束了一个半月,距离分数出来也有一个月了,而前几天考生们也得知了自己的去向,无论满意的或不满意的,都带来了欢笑或泪水、喜悦或悲叹。录取通知书的到达,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通知,更带有着某种审判的意味:他们从此就被打上了烙印,从此,他们就要背负着这份录取通知书在这个社会度过余生。
不满从来都有,但这次的不满颇有点乌龙意味。一名贵州的考生,总分631分,省排名2206位,应当说以一个还算不错的成绩,被厦门大学(属于985高校)录取了。结果,这个“厦门大学”并不在厦门,而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区”。
于是,该考生选择发帖。结果发现,与他一样的还有17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遂要求维权,但贵州考试院则一口咬定:志愿书中明确区分了本部与分校,且专业代码不同,填错了是你自己不认真看导致的。在解决办法上,双方倒是统一的:退档、复读。
人们评价,现在的情况是三输:那些误报的考生要多耗费一年的青春;本来报了厦大马来校区的考生被挤了下去;厦大马来校区的招生名额被浪费了。过错造成的道德后果总要有人承担。
选择错了?
一种声音说:填报志愿这么大的事,你不好好关注,你填错了,又能怪谁呢?活该。为了对抗那些具有朴素道德情怀的人,他们还发明一套理论,即:填报志愿也是筛选的一种形式。这些人没有关注到厦大本部与厦大马来分校的差别,其实也是被筛选掉了。这种论调引来了一些反驳,因为它听起来毕竟太绝情了。
我们当然可以用各种事实来反驳这种观点,比如相比其它有分校的高校,贵州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相关的填报界面确实不够明显;厚厚的志愿书翻阅起来也并不方便等等。但是这种反驳并不能根本上驳倒对方,他们总可以再问:为什么那些考生就不能再多看一眼呢?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再确认一遍呢?因此,纠结考生究竟什么程度才算细心是徒劳的,实际上是被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统摄住了。
这种观点其实是在说:人应当为自己做的选择负责。自由选择是你的权利,相应而来的义务则是承认你对选择的结果负有道德义务。这一套准则听起来很诱人,事实上也是很通用的,因为它构建了一套解释社会的方法——它先把社会分解为个人,再依据每个人的选择去评判他。
我们可以看到,选择作为一种道德原则隐含了不少预设。首先,当然是“人是自由的”,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活动。但我们要注意到,这是一种庸俗的自由观。区别于主观能动性,这种自由宣称自己具有普遍性:它作为一种形而上的能力,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而非高级的、复杂的物质系统自行运作的结果。这条预设本身就埋下了错误的根基。仅仅宣称人是自由的,还不足以将道德责任加于选择者之上;这就引出第二条预设:选择不是指单向的选择,而是双向的。比如本次事件中,不光考生报考学校也是一种选择,学校也在依据分数选择学生。而这种双向的选择,作为一种互利的手段,事实上等于契约。因此,所谓的“选择责任论”,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契约论,为选择的后果负责,就是遵守契约的内容。
契约精神中似乎蕴含了平等的可能,因为签订契约的双方遵守的都是同样的原则。如此一来,错误似乎更多在考生身上:你既然签订了契约,又怎么能随便就反悔呢?但是,在实践中,这种精神的实际效用仍然值得考察。
当然,契约论者不会否认选择之前必须有充足的信息,否则连诈骗都能被归为自愿选择的结果。因而信息充足与否是影响一个选择是否有效力的重要因素。认为“没有标注清楚因此贵州考试院占主要责任”的人,便是从信息差的角度出发,论述贵州考试院的责任。
也应该注意到,这种辩护策略并不稳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基础信息很容易就能检索到。因偶然而产生的信息差已经越来越少。但是仍然存在必然的信息差:企业与公共机构等以一种极不透明的方式运行,向外透露的所有信息都经过严格的筛选与修改。结构性的信息不对等似乎又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某些“机密”的存在与尚未公之于众的战略规划,愈演愈烈的贪腐行为,旁门邪道的歪路子,生产的关键步骤,以及一些事件的真相,官方可以掌控,但绝不能透露——结果契约原则反而说明了当下的体制存在着不正义之处。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连信息差也商业化了——高考咨询服务每年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段盛行,动辄上千元,养活了多少“知情人士”;知识付费大行其道,各类网课满天飞更别提各种掌握专业知识的人,一要价便是狮子大开口……尽管可以被市场解读为“服务业”,但是过度泛滥的信息似乎在告诉我们:持有信息或知识也是一种能力,你并不是一个在所有的选择中择优而持的自由意志主体,相反,你不过是在盲人摸象,只不过付费可以让你看到更多的门道。对于没有能力付费的人而言,成本则会以另一种形式加在他们头上。资本主义以这种方式进一步加强了统治阶级的特权,又回过头来践踏了自己的道德。
选择与没有选择
那么,是否像自由派说的那样,建立一个最小的“守夜人”政府,实行他们所谓的民主,事情就能解决呢?情况恐怕也没那么简单。就好像误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这件事,若不深究,无非就是那几个人该不该多看一眼的问题。然而我们还要看到,这件事在贴吧冲上热搜榜第一,大肆宣扬着它多么异常,就好像其它正常填报的考生都进行了一次完美的选择。
选择要成为一种道德原则,绝不是因为选择本身的魔力,而是选择本身确实能够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选择才成为了一种道德原则,用来维护用“契约”支撑起来的社会运行体系。上世纪末下海经商的选择、本世纪初创业的选择、有闲钱的人家投资炒股的选择,到填报志愿的选择、考研读博与否的选择,考公考编的选择,乃至于上哪家公司的选择……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选择充斥我们身边,维护市场体制的人也视这种选择为骄傲,说什么只有保证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让他们自己走向更美好的生活,社会就能自动地达到最佳的分配。
于是,高考生们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前提是哪所院校能要他;打工人们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前提是哪家企业会接受他。然而,高考生们除了选择某一所院校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不是这样就找不到“好工作”;打工人们除了不断投简历别无选择,因为不是这样就没有饭钱。社会并没有达到最佳的分配,相反,它在开放选择的前提下束缚着选择,它提供的所有选择,都在维护这个秩序的基础之上。结果,人们确实在选择,但只是在物的统治下被逼迫着去选择;人们确实在签订契约,但只是零零碎碎地把自己卖掉罢了。
更进一步地说,尊重选择、尊重契约,无非是要尊重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要保留资本家们有未经他们允许就不能剥夺他们财产的自由。要考生签订这种“契约”,本质上也是要求考生不能在未经院校允许的情况下“窃取”院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与毕业证书。在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区更是这样:虽然据说它的教学水平与本部齐平,毕业证书也完全一样,而那些考生却拒绝了它,除了对出国的顾虑外,还有对高成本的担忧:国内多数大学一年学费大约五六千,但厦大马来分校一年学费高达四万,生活成本也偏高,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它的学费高昂,但往年分数却远低于厦大本部。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哥伦比亚大学下辖的巴纳德女子学院,从社区大学就可转入,毕业证书却是同哥伦比亚大学一样的文凭,协和医院的董小姐不就是用这个途径成为了“海归高材生”吗?国内很多大学也存在这种分校,如人民大学苏州分校——这种低分高费的分校存在本身,就是提供一种方法,让家境富裕的学生获得更高的文凭。它不仅破坏了高考规则中优绩主义规则本身,也向人们宣示在选择之前就存在的不平等击碎了选择作为道德原则的正义性。选择权永远会留给统治阶级,因而他们才会说“尊重选择”。
过去的诸多选择确实造就了不少权贵,然而它事实上是在越来越缩减劳苦大众拥有的选择权。当我们面临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时,犯不着自怨自艾,认为是自己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相反,我们要让选择突破统治阶级给出的限度——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同样是我们的可选项,并且越来越成为仅剩的选项。届时,我们的选择就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生存,更是确证自己属于无产阶级这个大集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