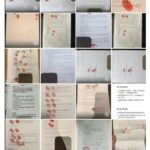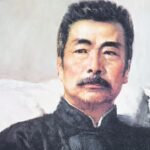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许多马克思主义青年时常被人挑战:你要弃家人于不顾吗?若果你投身革命,那你的家里人要怎么办呢。诚然,我们许多同志都在这个问题上被框住了手脚,我们不可能绝情到说完全不会再理会家人的处境了,这也是不现实的,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不鼓励的,尽管下文会阐述家庭这种生产单位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罪恶之处”,但是不代表辩证唯物主义者完全否定家庭的一切——至少我们绝对不可以否认血缘关系带来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的纯粹和伟大不容任何学派的人染指和曲解。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维护这种最纯粹的伟大,现实的问题依然还是赤裸裸地摆在我们眼前——我们高度和家庭挂钩,这直接牵涉到了我们的革命——我们的革命在第一步,就必须要进行对家庭的审视和考量,我们首先要跨出去!家庭这第一道坎,它究竟是为什么成为了我们革命的第一道阻力,致使我们不得不为此牵挂,或者是被其限制,或者是受其掣肘。
这道坎首先表现在物质生产上:个人高度和家庭挂钩,如前文《关于学生》所说的那样,尚处于求学阶段的马克思主义青年的生存仰赖于其来自的家庭;已经参与劳动生产的,则是要承担起维持家庭运作的责任(同样,提出极端家庭例子的论调不在少数,不过这是不经大脑的低级趣味反驳,在分析完一般典型家庭之后,极端例子只会是更加差劣),在这里,我们观察到家庭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虽然是社会的性质,但是生产家庭成员再生产的生产,却是家庭自己的事情。社会的生产没有责任照顾单一家庭生产,但是家庭的生产却要为了社会生产付出所有,否则这个家庭将难以为继。因此,尝试在物质生产上脱离家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生产上的立足难度将会霎时变高,因为他不仅要负责社会生产的其中一部分,同时还要负责生产自己的再生产。那些出色的青年往往只在少数,而大部分的青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像社会十分排斥有单一个体从家庭中脱离出来,不受家庭的控制,从而用“各种力量”势必要把这些青年束缚在家庭这个基本的生产单位里。
那么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既然社会生产抗拒为单一家庭再生产负责,而社会生产的成果,在波拿巴主义中国下又展现了饶有趣味的私有性,因此排斥为单一家庭生产负责的,不是社会生产的过程,而是社会生产的占有。即,已经以极其令人作呕的形式交媾在一起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官僚和其他特权阶层,拒绝在打着真正的社会主义旗帜的领导下让家庭逐步消亡的责任,反而无所不用其极地以任何手段,使单一家庭这种分裂的社会生产单位,在社会生产中处于无限接近隔绝的状态,并确保不会有人从这种形式中脱离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喉舌的中国共产党希望确保存在一个十分稳固的家庭形式,这并不是因为它很关注每个家庭里面那种属于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这也是许多同志想不通的一点,他们或许会发问:“难道我们可以忽视现实里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吗?现实里的家人之间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情感,完全基于物质生产呢?”不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家庭成员的情感纽带天然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社会制度的存在的,但某种社会制度的存在天然需要这种家庭成员的情感纽带。正如火是人类文明的开端,却也是人类之间杀戮的工具,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天然成为了中国的波拿巴主义制度下剥削的最好工具,它帮助了资产阶级不费吹灰之力将个体和家庭紧紧捆绑在一起。
可是这样做对剥削阶级有什么好处?
在回答这个最终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再用另一把手术刀切开这个,独属于中国家庭的“肿瘤”。中国经历了千百多年的专制王朝时代,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农业都是第一生产,因此,千百年来的社会生产的形式,一定是契合农业生产的。所以,在专制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的家庭形式通常规模会趋向庞大,这是因为:生产力落后的同时,规模较大的家庭——甚至广义上来说,可以直接说是宗族,抗风险的能力会很高。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社会生产进入农业时代后,男性天然成为了一个家庭里面的中央枢纽,女性在农业的社会生产模式中处于劣势,因此只能回归家庭服务于再生产,一个围绕着“父亲”的家庭形式(这个家庭甚至可以扩义,基本上整体社会和国家都是类似的形式,不过为了方便理解,先集中在家庭)就形成了。接下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宗族,或者说家庭的维持,必须确保物质生产能在这个范围内得到继承,也就是必须确保家庭成员对于父亲一系的枢纽表示忠诚。答案很显然,这种绝对忠诚的要求,来自于统治阶级最推崇的孔儒之学(金银天生不是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当然,无论怎么看,这种要求全部家庭成员都要为一系的中央继承系统服务的机制显然是反人性的,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不少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窥探到,我们可以从专制主义历史上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窥探到,她们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完全丢失了社会生产的主导权,甚至因此沦为家庭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不错,家庭专制主义甚至会把人异化成了生产资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性通常被当作政治手段,作为利益集团连结的售卖品,也就是所谓的“联姻”。同时,专制主义也将男性异化,他们如若不能在家庭的扩大生产中胜出,那么也只能沦为胜者的奴隶,其地位甚至低于现在的自由劳动者——他们的全身心都隶属于占有他们的人。因此,孔儒之学所推崇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为前资本主义下的专制制度中的家庭的维持而服务的,因此它极度排斥任何对于这个机制的反抗和批评,它推崇服从和孝顺,它推崇尊卑有序,年长的对于后辈掌握绝对的指导权和控制权;反过来,后辈在这样的社会生产下别无所依,脱离家庭生产将失去他们唯一的庇护,在那个生产力如此落后的年代,脱离出去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物质上又不得不迫使他们留在家庭,然后将这个“剥削”不断维持下去。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为人所歌颂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一不都带着对这种扭曲的专制主义的反抗和呐喊(梁祝、白娘子、水浒传、西游记等等)。
因此我们到这一步终于可以观察到家庭的大概,社会生产的结果通过物质和精神两个手段,尽力维持这种稳固的家庭形式,迫使社会生产上的个体都必须高度和家庭形式连结。
我们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对剥削阶级到底有什么好处?
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如前文所说,社会生产的结果不需要为家庭生产负责,但是家庭生产就必须要依附于社会生产,否则它将难以立足——这说明,高度和家庭连结的个体必须更加异化自己,他必须接受更为苛刻的工作条件,他必须对资产阶级无限服从,以换取可以维持他和他所在家庭立足的工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被束之高阁的孔儒专制,将个体禁锢在家庭之中,并用人类天然的亲属情感联系作为包装,对劳动阶级进行精神生产和具体、抽象劳动生产的剥削。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负责赚取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的劳动者,他们的处境十分糟糕,肩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同时必须在外对资产阶级唯命是从,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作机会,他必须变得自私,甚至可能对同样处境的劳动者们进行无情算计,并从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聪明的同志这个时候就会提出疑问了,既然如此,那所有能参与劳动的成员都参与社会生产不就可以了吗?事实上,这并不是资产阶级希望看到的景象,一来它必须控制一定的失业人口以更好地控制正在劳动的劳动者;此外,正如恩格斯所描述地那样,资产阶级渴望尽可能少的家庭成员参与社会生产,这样它们就不用负责那些负责生产家庭再生产成员的生产。因此可以观察到,失业率永远是官方机构最关注的数据,他们会极度鼓励个体不断形成新的家庭,他们鼓励结婚生子,并十分期望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中被淘汰的个体以各种形式回归家庭(家庭主妇),这样,生产再生产的劳动,也就是负责家庭再生产的劳动,资产阶级就不需要为此负责了,他们只需要给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者支付工资,而不需要为家庭主妇支付什么,这样他们平白无故就获取了额外一份劳动成果,这一部分成果,如前文所说,就属于社会生产不为家庭生产负责的来源。同时,这也解决了失业率的问题。因此,越是经济下行,资产阶级就会越是鼓励个体组成家庭,因为一旦组成家庭,劳动者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如同自行戴上镣铐,任由资产阶级予取予求了。
矛盾论再次展现了它迷人无比的一面,资产阶级越是推崇它所喜爱的最大化自由度的市场,它所渴求的家庭形成就越是失去物质基础。产业升级和劳动分工的细化,进一步摧毁了家庭形成的必要性,信息技术的革命又钉死了它的棺材板。我们发现,商品经济越是发达,则个体对家庭形成的需求就会相对农业生产时期要减少许多,这是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力要求有相应足够高的消费能力去消费它的生产,这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样:物与物的关系开始凌驾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往家庭的生存物质提供的职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这个职能被市场交易分割出去了一部分,无产阶级个体无论是否愿意遵循他的家庭内先进的或落后的规训,或是他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如何,都不影响他是市场上的“自由人”,只要他愿意,总能通过参与雇佣劳动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了青年人和他家庭的依赖解除,除了提供物质上的脱离可能,在这一个步骤最关键的是——资本主义剥夺了家庭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职能,现在它由统治阶级所制定的义务教育和社会生产中的人的互动来承担。以往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产的职能可以说是被完全分割了出去。由于精神上的依赖被完全转移,青年人的意识形态就会很自然浸染了市场上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易的意识形态,尽管它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21世纪10年代以后,社会生产的意识形态和旧家庭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展开激烈交锋,具体表现在一代年青人和家庭长辈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他们开始关注自己是否在家庭当中得到长辈的尊重,而不是像个傀儡一样全部都听父母媒妁之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青年人为此思想斗争付出惨重代价,轻则落下心理疾病,重则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进程。
因此,尽管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现在年轻人是否愿意结婚生育、或者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的中共的政策是否愿意为家庭形成提供足够支持,事实上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早就已经摧毁了家庭形成的经济基础(或者说摧毁了家庭形成的必要性,放在以前如果不能组织起家庭,那么个体生存的难度将会非常高,但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则允许了个体在理论上有无须组成家庭的可能),更遑论现如今组成家庭所需要的成本和代价了。
矛与盾中的矛与盾
现在我们知道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一边渴望个体能够形成家庭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被剥削,一边不断渴求更加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但这同时又会摧毁家庭的组成必要性,这是宏观上的矛盾。
现在我们再集中聚焦,现在家庭组成的过程,也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个异化的过程。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人类的自然情感属性,恰恰相反,辩证唯物主义绝对不会否认人类天然的情感联系,抛却任何人类自行拟定的乱七八糟的程序规训,任意两性之间产生互相欣赏和互相爱慕的情愫是如此的美好和自然,而正正也是这种情感,才使得我们人类成为人。不单单是爱情,友情,亲情,人类天然的情感属性促使我们能够为此发挥最为强大的主观能动创造力:爱人之间表达爱慕促使了许多浪漫的诗句,为了厮守一生和社会作对;双亲在危险之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儿总是可以爆发出超越自身极限的力量;知己之间可以发展出“非高山而不流水”的断肠共鸣。正是这样的情感才促使人类如此独特。
而资本主义的罪恶之处就是它总是将物与物的交易、货币交易凌驾在人与人的联系上。我们来观察下现在中国青年人的家庭形成过程是怎么样被异化的:两个年轻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他们在生命中的某个节点相遇,相知,然后相爱。在经历了一定的相处时间后,他们认为对方是合格的伙伴,在社会生产中可以进行互相协作,共同生存,最重要的是——他们非常相爱,那种天然的情愫使他们难以割舍和分离。
但是问题来了,他们不能就这样宣称他们相爱了,不能就这样将双方仅有的物质组合起来协作生存,在今天这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下,他们必须走一些特定的社会程序来确保家庭的“合法性”。首先,他们必须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对即将形成的家庭予以统治阶级的权力保障,也就是所谓的“领证”,一旦领证,即说明基本生产单位形成,这个单位必须遵循统治阶级的规训,受统治阶级法律监管和保护,或者解锁一些个体没有的,而一个家庭生产单位才能带来的政策福利(理想下假设存在)等等。但是,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两个即将形成家庭的个体本身就来自于两个不同家庭,我们假设两个个体都从原来的家庭中脱离而形成新的家庭(就算不假设也一样,下文继续)。
潘多拉的盒子就是在这一个步骤被打开了,无论怎么样,这个新的家庭形成过程不知怎么的就一定要牵涉某个家庭成员从原来的家庭中脱离:要么就是女性从原来的家庭中脱离,并入男性家庭(我们叫嫁娶);要么是男性脱离原来的家庭,并入女性家庭(我们叫入赘);要么就是一齐脱离,形成新的家庭。明明是基于人类美好的天然情感而促成的良缘,但是似乎组成的步骤不同,它就变了种一样,为什么这个过程如此关心具体是哪一位成员从原来的家庭当中脱离,为什么同样是相爱,却被某种诡异的力量套上不同的名字呢?难道说,“嫁娶”的爱,和“入赘”的爱也有区别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反直觉的,人类的情愫怎么可以量化呢?那么当中到底是什么被量化了?
是物质被量化了,关键的一步不在于新家庭的形成和新成员的加入,而是旧成员的脱离,是旧成员的脱离所涉及的物质分配,在家庭形成的过程中迅速凌驾了人的情感连结。旧成员的脱离对于旧家庭来说是重大的变动,在以往农业生产时代,成员一定是生产力的一员,女性由于在农业生产中丢失主导权,因此被迫成为父系继承系统的消耗品。诚然,一个专制主义家庭怎么可能白白让女性成员出嫁,甚至还得自掏腰包支付“嫁妆”呢。抛却那些繁杂的“三拜天地”,“八抬大轿”,家庭于是很自然地就想到了纯粹的物质交易,要么就是这样的嫁娶使得家庭进行融合和连结,成为更庞大的宗族势力,这对原先的家庭来说都有好处;要么脱离家庭的个体的家庭就会根据实际的物质基础要求对方家庭以对等的物质来进行交换,这里甚至还是假设“喜结连理”的一对新人是两情相悦的情况,也就是说,就算这对新人完全没有任何情感基础,只要物质条件允许发生反应,那么这个进程也可以没有障碍地运行,因为在家庭专制主义的规训下,这对新人没有反抗家庭使命的权力。这样,无论新人的情感基础如何,此时此刻都不重要了,新家庭形成完全依赖上旧家庭的意志,取决于物质条件是否合适,一旦合适,那么就可以达成商品交换,成员被明码标价以某种价格售出,换取旧家庭在社会生产当中的资源。
那么在现在的时代呢?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动,首先是组成新家庭的物质必要性被消解了,即使不组成新家庭,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无产阶级都可以从社会化大生产中取得,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其次,由于家庭的精神生产主导权被社会生产剥夺了,青年人又不必非父母之言不可,家庭形成看似完全依赖个体选择了。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似乎比封建专制要和善许多,它大手一摊表明自己没有责任为个体的婚姻负责,它允许鼓励婚姻自由。但是,资产阶级的婚姻恰恰是最不自由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对于物质继承的要求和渴望甚至比前资本主义的宗族还要极端,因此资产阶级是绝对不轻易允许婚姻“扶贫”的,甚至他们的专制程度还要比封建专制时代要更进一步,对婚姻中情感因素的忽视更为彻底,直接清晰表明婚姻是物质交换的媒介,但凡不能从这场交易中有盈利,资产阶级都不会允许它发生。至于手段,那就更无需多言了,资产阶级渴望无产阶级组成家庭,所鼓吹的依然是被束之高阁的孔夫子。而底层的无产阶级呢?改革开放允许了东部沿海城市率先开发,在完成了城市化之后,工业生产迅速对中西部的劳动人口进行贪婪吸吮,中西部农业生产轰然倒台,加之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更使农业萎缩。同时,令人匪夷所思的计划生育政策掐灭了农村人口增长的最后一口气,那么那些没有外流到东部城市的人怎么办呢?面对萎缩的农业,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是“天子一念之威”,没有生产资料国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基础,没有落实到中国人民骨髓里的“文化革命”,使他们重新捡起了旧农业时代强悍无比的专制主义惯性——渴望人口,但是农村没有,那要怎么办呢?于是,中国在千禧年代向我们展示了道德彻底败坏的一幕:人贩子产业开始催生,他们成群结队,视女性和小孩为生产力,全国各地掳掠人口,造成无数家庭一生的缺憾。
而一般的家庭呢?它们就在社会生产的进程中,同时带有社会最上层和最底层的毛病,情况也是最为复杂的:我们似乎被允许婚姻自由了,但我们的婚姻真的自由吗?我们的婚姻本来是起源于人类最纯粹的爱慕,那是让我们人类之所以是人类的理由。现在它变得不那么重要,它只是催促了两个有缘人走到了一起,剩下的就没它什么事了。一般家庭,有的还在被前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扯着后脑勺的辫子,认为不结婚生子就不是正常人,在相亲市场中来回踱步;有的家庭互相之间已经开始纯粹的物质算计,完全忽略了新人的情感需求。无论是哪一种,人与人的关系都被物与物的关系凌驾了,诞生于人类最朴素的情感的行为,此时此刻和它的起源完全无关。并且,现在的统治阶级采用来自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维护其统治的现象,现如今竟然同时在这个经历过一次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洗礼的中国大地上每日呈现,这一切都要拜谁所赐呢?
我们终于揭开了中国的波拿巴主义制度下的家庭的神秘面纱,我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它会成为我们革命的阻力——它在精神和物质的生产上,都在不断地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成家立业”的意识形态教化深入每一个中国劳动人民的骨髓,并对他们的灵魂步步紧逼——一旦活到了某个岁数,只要没有结婚,整个社会教化就会对它无情鞭打,尽管他每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作奸犯科,他依然要遭受旁人的指指点点,或者是父母的专制威逼(尽管他可以是潇洒到完全不在乎任何社会规训),于是人们的焦虑程度就随着年纪上升和上升,越来越不顾及自己的真正喜好,在社会教化的逼迫下已经来不及建立任何情感连结,因此取而代之的,就是资本主义下最有效率的“商品交换”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婚姻,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它“商品交换”的本质,越来越展露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