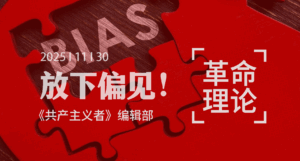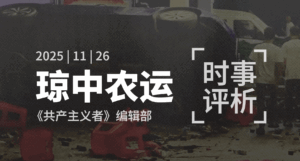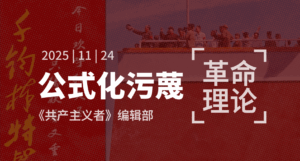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当今的资本主义在不断地把经济全球化,这也就导致现在的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也是全球化的,一国的经济危机会导致其他国家也遭受灾难,同样的,一国的阶级矛盾激烈化也反映了全球矛盾的激化。随着革命的进行,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因为工人罢工流向街头,工人阶级会发现自己成为了掌权者,为了适应自己获得的权力,他们就会自发地或者在工人政党的领导下组织起群众组织(具体例子如巴黎公社、巴伐利亚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巴勒斯坦大众委员会等)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一国革命胜利不代表任务结束,它只是世界革命的一环,世界工人阶级都会因此而充满革命热情,积极响应革命。同时工人国家也会积极地输出革命意识(但这不代表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输出革命没有任何冲突,而且,在世界革命成功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让其他国家的工人明白自己的利益和已经建成的工人国家是一致的。
我们要明白,阶级斗争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本质属性,由此延伸出一国革命的传播不是“给予”而是“激发”,即在于唤醒他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反对坐等革命条件“自然成熟”的消极态度,也反对越俎代庖的武力干涉(即单纯用刺刀输出革命)。为了输出革命,工人国家必须通过国际主义组织传播革命理论,构建跨国信息网络,将局部斗争经验转化为普遍认知模板。这种知识共享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帮助各地工人识别自身处境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关联性。此外,成功革命的范例本身就会产生引力,吸引其他地区进步力量主动效仿,而还未革命胜利的工人会通过国际罢工、抵制等非军事手段,对反动政权形成外部制衡,为工人国家创造活动和建设空间。
以下史实可以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1917年苏俄革命后,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而在1919-1920年,英国码头工人多次罢工拒绝为干涉俄国内战的军舰装载武器,迫使政府撤军;1920年波兰战争期间,德国铁路工人同样集体罢工阻断政府给波兰的军事援助,并声援苏俄。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53国4万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参战,包括美英法等未革命国家的工人。1960-197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法、意、日等国工人发动反战罢工,仅意大利1969年就有1800万工时罢工记录。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后,北欧多国工会发起抵制智利商品运动,并资助来自智利的流亡者。
我们先不提工人革命,就算是一般的工人罢工,都需要得到其他没有罢工的工人的支持,有时还需要其他工人一起罢工才能胜利,否则这场罢工很可能什么都争取不到,反而还为罢工的工人带来更差的结果。这是无数次实践所证明的。为了成功,罢工的策略也非常重要的。若是罢工发生在生产中关键的地方,达到目的的成功率会提高;若是没有争取生产关键位置的工人罢工,达到目的的成功率就不会高。同时,如果一场罢工的时间过长,基本上都会导致工人内部的严重分裂以及罢工工人的疲劳,最终导致罢工失败。
一般的罢工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由此,我们也可以把工人国家看作是一个正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罢工的一部分。工人国家即使采取防御姿态,其存在本身已构成对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否定。当它国有化关键生产部门、取消利润驱动机制、重构分配关系时,实质上在全球化商品链中制造了断裂带。这种断裂如同电网中的绝缘体,必然承受整个导电系统的电压冲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维持自身闭合性,必定试图消除这个异质节点——要么通过经济封锁诱发其内部机能紊乱,要么发动军事打击直接物理清除。如果认为工人国家只有打造所谓“中立形象”才能保障工人国家不被推翻,那就相对于要求罢工工人在罢工的同时遵守资方生产纪律,在逻辑层面自相矛盾。单独的工人国家的内部矛盾不会因为经济成就的增长而逐渐消失,这些矛盾反而会进一步加深,最终,工人国家就会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工人国家的生存概率取决于其引发的体系共振强度。若长期孤立存在,就必然面临双重绝境:其外部要承受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能量耗散攻击,内部因资源短缺被迫重建市场激励机制,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倒退。这种退化存在两种路径依赖:或是官僚集团为维持统治效能,将计划体制异化为新的剥削工具;或是生存压力迫使国家重新接入世界市场,复辟资本主义。避免这两种结局的根本出路,在于将自身转化为国际革命网络的能量中转站——通过技术共享、经验输出、跨国阶级动员等手段,将局部突破转化为体系性危机。
在落后地区成立的工人国家比在先进地区成立的工人国家更容易官僚化和失败,因为很多落后地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在工人国家成立后无法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相反,这个工人国家还会不断地受到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本地落后生产力带来的保守意识的影响与阻碍。这就是落后地区成立工人国家的危险性。先进地区的工人国家相关的危险会大大少过落后地区,因为它们所处的位置很可能会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的发达也更容易冲破保守的意识。但是没有其他地区的革命,这些工人国家也是容易走向失败的。(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一系列工人运动以及苏联的官僚化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在没有争取到先进地区的工人的支持时首先进行落后地区的革命。先成立的工人国家,无论它在先进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能大大鼓舞世界工人阶级。所以只要有国家出现了革命形式,我们就应该勇敢地把革命进行到底,为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不是什么从道德出发的理想,而是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思想意识。
随着世界革命的推进,建立的工人国家的相互帮助会直接解决经济问题,具体形式就是组合成一个社会主义联邦,也就是列宁提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使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成为单独存在的国家,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成为不久便能实现的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组织中的一个构成分子。列宁要这样是因为他认为:(1)这是俄国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果没有各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支持,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权是难于长期存在的;(2)这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问题。
在世界革命进展的条件下,如果某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它们必须以“联邦”形式结成极密切的联盟,否则,它们便不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中保持自己的存在,它们便“不能实现被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劳动者福利的保证”,不能“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以上引文见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八节)统一的工人联邦国家没有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对国内的职业化的决策机构就可以进行缩减,没有迫在眉睫的帝国主义威胁,国内的专政机器就会衰亡,这些都是建立在苏维埃的民主下实现的,一个国家机关的职能越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机关也就越来越没用,最终它会因为无事可做而在世界革命胜利后自行消亡。
我们并不否认会有民族主义倾向使得某些工人国家拒绝给予其他工人国家无国界的援助,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会让他们认识到这样合作的必要性,因为这样的合作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国家独自发展永远也达不到的。这就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单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其他地区的原材料和科学技术,没有工人国家之间无国界的互助,单个工人国家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资的引入充分展现了先进地区可以为落后地区带来何样的发展,而革命后显然不会是以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的形式实现的,而是以忽略国界的直接配置资源实现的。自然或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物质匮乏就是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在几年内解决。工人国家必须在实际上实行完全的民族平等。应该在语言、学校、宗教等等方面都实行这种平等。
不仅如此,工人国家应该实行充分的民族自决权,即给予任何民族的大多数劳动者以在可行范围之内来决定:这个民族是否愿意和其他民族留在一个国家的统一体内(可以选择建立民族自治区),或是愿意完全分离出来,建立该民族自治的独立的工人国家。而且民族自决权应超越单纯领土公投模式,转向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核心的复合型自治。列宁设想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合”应体现为:各区域苏维埃保留文化自治权,但生产资料国有化必须跨区域统筹,确保工人阶级整体利益优先于局部民族诉求。此外,在非洲经验也表明,几内亚比绍通过建立包含富拉尼族、巴兰特族的反殖统一战线,成功将部族认同升华为革命民族主义,这证明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关键在于将自决权转化为阶级斗争的组织工具而非地域分割依据。
任何一个国际主义者必然是赞同行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的。所谓行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无论个人或者国家,甚至不论其为何种人与何种国家,都是好的,应该的,因为这是一种工人阶级的独立精神与勤奋精神。如果不肯定这个方面的自力更生,那就等于提倡懒惰、提倡依赖、提倡靠天吃饭或提倡剥削他人、提倡坐地分赃。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不可能是由每一个大小不等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逐一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再像七巧板似的拼凑到一起后实现的,而是在很大限度内有赖于各国工人运动、特别有赖于已经获得胜利的工人革命,自始就着重于世界全局,坚持国际协作,以全球的视角来规划和建设暂时分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生产资料社会化需突破国界的客观事实证明组成工人联邦国家是一个必要政策,是应该无条件实现的,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可以因为“情况有变”而改变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