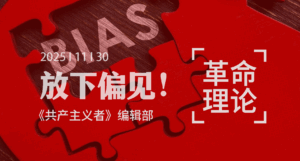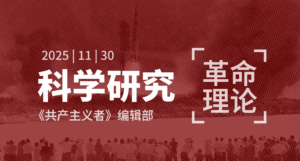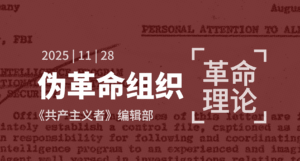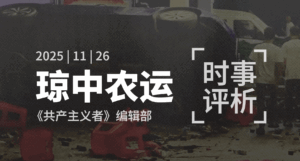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随着20世纪的结束,世界上仅有的社会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土崩瓦解。要不经历恐怖的内战和分裂,要不在动荡中伴随着“自由化”的口号倒退回了资本主义,乍一看社会主义的时代结束了,资本主义又重新在新世界站稳了脚跟。历史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否已经破产了?
反对共产主义、也是共产主义反对的这批人,高喊共产主义是一个不现实的乌托邦空想,在几十年的打闹后必然落下帷幕。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旧调重弹,认为马克思主义打着实现“理想社会”“地球上的天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全面和解”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激情,导致不择手段、国家专制主义的恐怖。这一来,他们就把出现于苏联、中国、东欧,甚至波尔布特的柬埔寨的例子,称之为共产主义不可避免的结局。
然而,这些都是无厘头的谩骂。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无神论的,因而不会也不可能有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说或“世俗化宗教”的成分。马克思主义没有天真地梦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实现全面和解,没有预言各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将来会完全消失,也从未企图强迫让人接受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通往奴役之路”这个公式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恶意虚构,它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从渐进政治的观点看所产生的后果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是不是乌托邦?把用在这方面的力量用于逐步改良现存的“开放社会”难道不更适宜吗?为举手可得的改良而斗争与追求“最终目标”及建立一个新社会之间,难道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吗?对统治阶级和国家进行全面批判并发起“强有力的”挑战,难道不会挑动他们抵制现行改良,甚至挑动他们报复吗?这样做客观上不是破坏了政治民主制吗?
这种对于乌托邦思想的诘难被用来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是对乌托邦一词的界定是有局限性的。倘若“乌托邦”被界定为不可能的或无法实现的理想,那么在政治上为乌托邦而斗争显然是徒劳的(尽管乌托邦还有一种道德上的意义),一旦我们与这种形式主义的、机械论的、非辩证的界定相决裂,“乌托邦”的含义也随之而变。前述定义在“可能”与“不可能”“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制造了绝对的对立。列宁在《怎么办?》曾提到“梦想的权利”,甚至“梦想的必要”,只要这种梦想涉及的是尚未存在、但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实现的事物。要使梦想成真,不仅要具备物质条件,而且需要努力、计划、行动的意志以及付诸行动的能力。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从未存在过,一些人以此为理由反对人类的进步。可是,废奴斗争是乌托邦吗?须知奴隶制的存在曾超过一千年。废除农奴制的愿望是乌托邦吗?宗教迫害,包括在火刑柱上烧死异教徒,至少在五百年时间内是一件“活生生的事实”。那么,试图建立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是乌托邦吗?在数百年间,议会制存在于非常狭隘的选举基础上,为普选权而斗争便是乌托邦吗?为什么废除雇佣劳动和庞大的官僚体制在今天便注定是乌托邦呢?雇佣劳动制和国家官僚成为社会结构的核心才不到两百年。在渐进的改良主义之外走一条捷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经验上看也是合理的。乌托邦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是逐步实现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之一。譬如以奴隶制为例,如果革命的或“乌托邦式的”废奴主义者局限于一个“特定制度”内为改良奴隶的生存条件而斗争,那么废除奴隶制当初就不会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常常混淆了科学预见与空想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将社会主义运动视为“乌托邦”的论调,实质上是将科学社会主义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认知谬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正在于它首次使社会主义从道德愿景转化为科学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发现其内在矛盾的运动规律,从而论证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必然性。 将社会主义等同于“乌托邦”的论调,本质上是对历史的辩证法的无知。当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时,同样经历了反复与挫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经半个世纪动荡,法国大革命付出八十年的反复代价。资本主义制度从萌芽到确立用了三百余年,而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其成长过程必然伴随更复杂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在于它提供了分析这些矛盾的方法论,而非描绘某个凝固的“理想蓝图”。
所以,在他们质疑共产主义是否可行前,笑话我们为之奋斗的新制度是空想时,共产主义者要先问:谁是空想?认为这个世界可以保持这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恐怖,认为除了社会主义之外能有任何方法去调和这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纵容资本主义继续吸食人血、破坏自然、堕落文化是可行的,这才是真正的空想。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并捍卫它的人,是真正的“反乌托邦”的信徒;而共产主义者,不是等待被解救、期待乌托邦降临的旁观者。我们是组织工人阶级建立新社会的革命者。
社会主义不会破产,它会遭到阶段性的挫败,资本主义同理。资本主义可以赢无数次,但社会主义只需要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