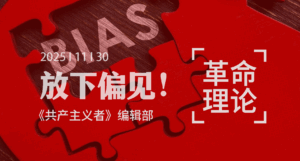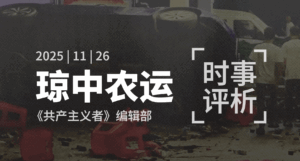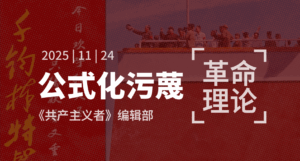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于5月22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宣布,哈佛大学学生和交流学者项目的资质已被撤销。这意味着哈佛不仅不能再招收国际学生入学,正在哈佛就读的外国非应届毕业生也必须转学,否则将失去合法身份。哈佛大学国际办公室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目前,哈佛大学招收了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0名国际学生和学者,国际学生占哈佛学生总数的27%以上,其中,国际学生中占比最高的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约占五分之一。
这份禁令并非毫无来由。早在今年1月,尚未迎来新总统特朗普的登基的美国政府,就曾向众多高校发出威胁;4月14日,哈佛大学拒绝遵从美国政府的多项要求,包括大规模改革学校管理层,修改招生政策,关闭校园内与“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相关的项目等。美国政府随即宣布冻结哈佛大学22亿美元多年期拨款。5月5日,美国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表示,联邦政府将不再对哈佛大学提供新的资助。5月13日,美国政府表示,八个联邦机构将终止向美国哈佛大学提供另外4.5亿美元的拨款。这意味着哈佛大学的财政问题最终还是走到了不得不完全依靠自身的紧要关头,而受这份禁令所影响的国际留学生,“碰巧”是哈佛大学经济收入的重要一环。
一方是高呼学术自由的高校,一方是强调国家安全的政府,其间的冲突并不如表现出的那样局限于行政管理上庸俗的官僚矛盾,而是反映着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各阶级围绕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的的持久博弈。
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即承诺整顿高等教育,他指控包括哈佛在内的常春藤名校“成为激进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温床”,扬言要“夺回我们曾经伟大的教育机构”,然而事实果然如此吗?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除了归属国家机构为政权政策摇旗呐喊之外的,包括家庭、公共媒体、学校等在内的社会机构,都是构成精神生产资料或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的一部分,其生产内容的本质最终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根本决定,和国家机器一样并肩凌驾于社会之上基于经济基础发挥其作用,而非表面上的单纯的政权意志的延申。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和国家机器之间屡有以王权与教权之争为代表的矛盾,在现代这个矛盾以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的形式得以再现,揭示了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根本触动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延续。
美国政府辩解自己的禁令是针对哈佛校园内“反美、反犹太支持恐怖主义煽动者”给出的,后者可以明确地被定位到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哈佛校内支持巴勒斯坦解放、反对以色列种族灭绝暴行的英勇的学生群体。特朗普猛烈抨击哈佛大学拒绝接受政府在招生和聘用方面的监管,并多次声称该校充斥着反犹主义和“觉醒”的自由派意识形态。不仅如此,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哈佛大学需要“为在校园内与中国共产党协调行为承担责任”,而这一切都于美国自上世纪庇护逃离欧洲纳粹崛起的高级知识分子时起标榜自身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民主灯塔的形象背道而驰。
这时候资本主义宣传的“自由民主”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暴露的一览无余。即使在最开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自由和民主也只是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的一种手段,而非其所信奉的“真理”。列宁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可见作为欺骗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制度会允许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以确保权力稳固;但在社会动荡、群众大规模激进化、不满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他们则不得不收回昨日的假笑,掏出棍子来教训不服从者。自由灯塔、学术自由的港湾,就因为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基地”。
进步学生掀起的富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声援巴勒斯坦反种族灭绝运动曾基于各美国高校对美国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舆论影响,这事实上也体现了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的掌握和争夺始终在贯穿人类历史始终的阶级斗争进程中动态博弈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哈佛大学这一超精英大学同时培养统治阶级和投身工厂企业的技术类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得到自然化的确证,即再生产不同阶层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持续在个体实践层面复现“政治权力”的分配,将人固定在围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等级秩序中。然而,先进知识分子的得以接触到激进的进步思潮并受之影响,是走向末路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到处出现的自然而然的现象,这意味着客观历史进程将要借助历史主体辩证地得以表现,是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本身身处资本主义教育体系制高点的哈佛大学,轻易就能成为意识形态变革领域的领头羊,无论这个变革的具体性质如何;学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自身的高台之上创造性地发出自己乃至社会的声音,将意识形态灌输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变为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战场,矛盾走向激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知识分子自然走向激化寻找其他的出路。
美国政府将矛头对准国际学生,既是扼住哈佛最后的经济支柱的尝试,更是在维持知识霸权垄断,在大洋彼岸复刻老对手中国的“境外势力论”。为了呼应国内右翼保守选民的诉求和兑现特朗普发现越来越难兑现的竞选承诺,特朗普政府还给哈佛加上了一个别样的罪名:“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而后者恰好是坏蛋民主党的得意招牌。面对经济颓靡,民众不满日益加剧的社会现实,特朗普政府不惜继毁掉自己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和外交上的形象的同时,再毁掉学术自由上的形象。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将会被暗戳戳地视作在美国煽动不和谐因素的“境外势力”,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标靶,为美国社会的矛盾激化负责。学术已经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筹码和执政不力的替罪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通过解雇拒签反犹声明的教授换取了豁免,而哈佛因坚持学术独立遭受制裁,这种选择性打压揭示了资产阶级法律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弹性本质。教育机构标榜的“学术自由”在资本权力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所谓“知识中立”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已被国家机器彻底撕破。
我们重申以学校等机构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的阶级即生产关系本质,更强调国家机器在转移国内矛盾和确保自身政治利益上所使用的手段的不遗余力。真正、彻底的学术自由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得以实现,在国家机器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的社会里,学术研究将不再受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政治利益的操纵,而是纯粹地为了人类的生产力,即改造自然的能力服务,如果说他再生产了什么生产关系的话,也只会是确保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生产关系。
走向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造就了意识形态变革的基石,然而这块基石也必须矗立在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变革之上。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党的领导,进步分子零星的抗议运动是不可能导向一场能够取得成果的革命的。组织起来,为推翻根本制约着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属于群众自己的解决方案而战,应当成为一切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