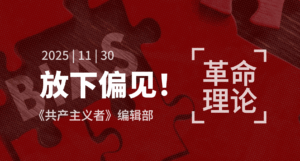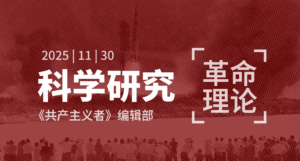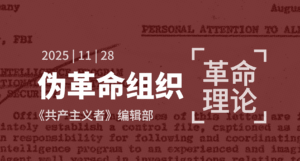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TG频道链接:https://t.me/revcommunist0cn
“你支持女性主义吗?”
“我不。我是共产主义者,不是女性主义者。”
“啊!国男、吊子、劳保,你支持父权制,你压迫女性!”
“……”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长久以来在性别问题上因为拒绝加入身份政治的行列遭受这种谩骂。这还不只是性别议题,在民族、种族等等领域,小资产阶级运动家们用道德和自己的“身份”逼迫严肃的革命者在他们的领域里“听从他们的计划,遵守他们的规矩”。他们的世界观是无理的两极,自己这片代表着进步与解放,而其他任何人都是压迫者和反动派。
实际上身份政治对于中国群众的影响严重吗?不严重,而且遭人唾弃。但是在共产主义者自己的队伍里,却因为这种异阶级的压力创造了无数困惑。要不是半懂不懂应和着身份政治的口号,认为“既然都是进步那应该没啥大问题”,要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接受自己的保守心理去正当化压迫,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反对身份政治。我们有必要从理论根基和实践行动上彻底批判身份政治,并解释共产主义的立场。
家庭、性别、性取向
21世纪生物学研究显示,性别差异存在部分生物学基础。神经影像学证实,男女大脑在胼胝体厚度(女性平均厚10%)、杏仁核连接方式上存在统计学差异。内分泌学研究证明,胎儿期睾酮暴露水平影响空间认知能力发展,催产素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共情能力呈正相关。表观遗传学更发现,社会环境压力可通过DNA甲基化影响性别相关基因表达。然而,2025年的研究进展彻底否定了“性别二元论”,揭示性别在生理层面是一个包含染色体、激素和解剖结构的连续光谱。染色体层面,除典型XX/XY外,特纳氏综合征(X)、克林费特综合征(XXY)等广泛存在,且美国最新研究发现,Y染色体并非男性化的绝对保障:XY个体可因SRY基因突变发育出典型女性生殖器。因而,我们需注意三个关键点:(1)这些差异呈现重叠分布而非二元对立;(2)个体内差异远大于性别间差异;(3)神经可塑性使大脑结构随经验持续改变。多项PISA研究证实,在性别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如挪威),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越小,甚至出现女生反超男生的现象,而在性别刻板印象较强的地区,男生数学优势更显著;2025年《自然》研究证明,环境压力通过DNA甲基化调控雄激素受体表达,且导航训练6个月后两性海马体体积增长无统计学差异。这些都印证了生物学基础与社会实践的交互性,生理差异如同未雕刻的大理石,社会文化则是塑造雕像的刻刀。综合2025年成果,性别差异本质是染色体多态性、激素动态平衡、器官特异性应答与环境暴露交互作用形成的多维谱系,任何简化二元框架均与事实相悖。
在人类早期社会中,两性关系以互补协作为核心特征。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经济中,女性通过采集植物和照顾后代贡献约60%-70%的群体食物来源,男性狩猎则提供蛋白质补充,这种基于生理差异的自然分工并未形成等级压迫,反而构成了生存必需的合作关系。考古证据显示,距今3万年的欧洲格拉维特文化遗址中,女性墓葬随葬狩猎工具的比例达30%,表明性别角色具有流动性。这种平等性源于低水平生产力下的生存逻辑——群体存续依赖全体成员的劳动参与,个人脱离集体即面临死亡威胁,权力集中既无必要也无物质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成为转折点。野生作物驯化需要持续的土地开垦,男性因肌肉强度优势逐渐主导耕作,而女性因生育周期被束缚于家庭领域。西亚加泰土丘遗址的谷物加工区集中分布在家户内部,暗示女性劳动被私有化。更重要的是,剩余产品积累催生了私有财产观念。当长江流域良渚文化出现玉礼器垄断性随葬时,男性墓主占比达85%,显示物质财富开始通过父系传承。牲畜饲养的普及进一步强化此趋势——非洲富拉尼人的研究表明,控制牛群的男性通过“牲畜借贷”构建债务网络,将经济权力转化为社会支配力。
制度性压迫最终通过战争与宗教完成体系化。苏美尔城邦为争夺灌溉水源频繁发动战争,职业军队的出现使男性垄断暴力机关,乌鲁克神庙壁画中女神逐渐被持剑男神取代便是象征。印度《摩奴法典》将女性定义为“需终生受监护者”,中国商代甲骨文记载的人祭中女性占比超70%,皆表明父权制通过法律与仪式完成意识形态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具有区域性差异:北欧维京人长期保留女性财产继承权,而西非约鲁巴文化中女性直到19世纪仍掌控市场贸易网络,证明性别压迫并非历史必然,而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
现代机器的轰鸣最终暴露了性别分工的荒谬本质。珍妮纺纱机的出现使纺织业从家庭作坊走向工厂,打字机的发明让文书工作不再依赖男性握力。当化纤面料取代手工纺织,当试管婴儿技术突破生育束缚,传统性别分工的物质基础早已崩塌。但父权制的幽灵仍在通过文化惯性延续生命:硅谷算法工程师中女性占比不足20%,并非因为神经网络需要雄性激素驱动,而是女孩在12岁时就开始接收“数学不适合女生”的心理暗示。这种文化塑造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2018年MIT实验显示,女性在匿名编程测试中的代码质量评分会突然提升46%。
马克思主义认为,组成传统家庭的婚姻在阶级社会中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它主要基于财产私有制与继承权的维护,而不是基于爱情,因此传统家庭中的性行为往往被异化为服务于财产关系再生产的目的。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单元,家庭在古代社会承担着直接的物质生产与人的再生产双重职能,其结构(父权制)通过土地依附、人身隶属等方式巩固等级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庭转型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隐秘工厂”,通过无偿家务劳动将工人子女培育为合格劳动力,将工人配偶转化为照护者,使资本得以用最低工资获取完整劳动力体系。可见,家庭一直依托内部权威结构(父权/夫权)塑造服从意识,为阶级统治提供文化基础。
在阶级社会条件下,古代宗教(基督教、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通过其道德规范将这些关系神圣化,并且将性行为严格限制在生殖目的范畴内。(堕胎也因此被视为对既定社会秩序的破坏)宗教道德体系将非生殖目的的性行为视为违背自然秩序。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手淫、口交、肛交、同性恋、跨物种性行为等非生殖性行为都被纳入道德谴责范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摧毁封建生产关系,封建宗法制的家庭结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家庭关系日益显现出契约化特征。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从世俗化的理性原则出发,否认宗教机构对道德价值的垄断解释权。他们反对“唯有生殖目的能使性行为合法化”的观点,主张:婚姻契约应当基于个体情感,并且允许婚姻契约因情感消亡而解除。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通过继承法、劳动力再生产机制等使得这些理念存在内在矛盾。在意识形态再生产层面,传统家庭的权威结构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仍具有功能价值。通过家庭教育塑造的子女对父母的服从,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对雇主的服从提供了文化预设。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始终试图将个体的利益认知局限于家庭单位,从而掩盖工作场所和阶级关系的实质矛盾。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传统家庭的无条件维护和对非生殖目的性行为的道德压制都是维护阶级统治的表现。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家庭作为私有制载体的性质,主张消灭基于财产关系的婚姻制度,支持基于平等个体自由结合的新型社会关系、捍卫妇女对身体自主的掌控权,同时拒绝将性行为价值局限于生殖功能(涉及权力不对等或侵害他者权益的行为除外)。其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废除私有制消除家庭的经济纽带,将家务劳动与儿童养育社会化,以公共保障替代家庭财产功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全民福利体系中构建基于自由联合的平等关系,使情感纽带脱离物质依附。
此外,传统家庭的存在也带来了对LGBTQ+群体的压迫和歧视。然而,LGBTQ+群体的存在是自然且多元化的现象,其生物学基础与社会影响均表明,性少数群体本身与精神疾病无必然关联。国际权威医学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1990年将LGBTQ+从精神疾病分类中移除,强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本身并非病理现象。美国心理学会(APA)等机构明确指出,LGBTQ+群体的高抑郁、焦虑风险源于社会歧视而非性向本身,多项研究证实其心理健康问题与家庭排斥、政治攻击等外部压力直接相关。全球医学界共识认为,将LGBTQ+污名化为“精神疾病”缺乏科学依据且危害极大,需通过反歧视政策与包容性支持消除偏见。
研究发现,性取向与性别认同涉及复杂的遗传机制,例如双性恋行为相关的基因位点被发现可能通过促进冒险行为间接提升繁殖优势,解释了其在进化中的持续性。此外,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识别多个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位点,表明性取向具有高度多基因性。尽管早期“同性恋基因”假说存在争议,但科学界普遍认同先天与后天因素共同塑造性取向,而非单一决定论。此外,研究表明,性少数群体抑郁率显著高于顺性别者,而根源在于系统性歧视与暴力。例如,美国癌症协会报告指出,恐同症导致LGBTQ+人群回避医疗护理、加剧吸烟等高风险行为,从而间接提高癌症患病率;瑞典研究显示,双性恋女性遭受性暴力的风险是异性恋男性的49倍。此类社会暴力与“转化治疗”等制度性压迫直接相关,加州等地区已立法禁止此类心理虐待。因此,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与反歧视法律,而非质疑性少数群体的正常性,才是促进全民健康的关键。
关于家务劳动,马克思主义者们有以下见解:家务劳动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关系,它始终受主导的生产关系的支配(在资本主义下,家庭主妇的生活资料是通过自己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或是其配偶的工资获得的)。家务劳动的产品(即劳动力的生产)是不为销售而生产的,所以它的劳动过程不受价值规律作用的支配,即不受竞争的支配。没有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没有劳动借以获得抽象劳动特征的手段,而只有抽象劳动才构成价值的实质。劳动力不同于一切其它商品,它不是由任何劳动过程生产出来的,它是活的人类的一种属性,而活的人类是靠自己消费使用价值来维持生存的(但不是靠消费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其中有些使用价值就是由家务劳动提供的。另外,人们完全可以从市场上获得大部分家务劳动的替代劳动。如果在家中烤面包的家庭主妇生产劳动力,那末为出卖而生产面包的面包师为什么没有生产劳动力?如果我们把这一逻辑延伸一下,那末劳动力就会成为许多实业的产物了,劳动力的生产当然也就不是家务劳动特有的性质了。所以,家务劳动不生产价值,它当然也就不可能生产剩余价值,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家务劳动不能生产剩余产品,或不能以某种方式获得不是价值的另一种剩余产品。如果能够证明存在一种家务劳动所持有的剩余产品获得的方式,那末家务劳动才能是一种独立的生产关系。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并只不取决于其科技水平或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在于对弱势群体的态度。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以“自由”“人权”为旗号,但其内在逻辑却将人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女性、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系统性压迫的受害者。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达到历史高峰,平均每15分钟就有一名女性遭遇性暴力,而司法体系对此的纵容暴露出资本主义法律维护的并非普遍人权,而是阶级特权。墨西哥、阿根廷等地的贫民窟中,儿童被毒品集团控制,成为犯罪链条的牺牲品;美国威斯康星州甚至通过法案允许14岁童工工作至深夜,将劳动力短缺的代价转嫁到未成年人身上,这种“合法剥削”撕碎了资本主义“文明灯塔”的伪装。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必然导致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儿童在资本眼中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19世纪英国工厂中童工占比高达46%,矿场甚至雇佣4岁幼童,而今天的美国童工法案不过是这一逻辑的延续。老人和残疾人则因丧失“生产效率”被边缘化,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的本质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成本,而非真正保障人的尊严。
但压迫越深重,反抗越激烈。全球数百万女性发起“反对性别暴力”运动,拉丁美洲的“绿色浪潮”争取生育自主权,印度农民抗议中妇女成为先锋队,这些斗争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争取,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因为劳动的解放本身就包含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群体的解放。对于儿童,马克思主义主张由国家承担养育责任,提供免费教育和全面保障,终结“童工”这一文明污点;对于老人和残疾人,则通过社会化养老和无障碍改造,使其享有平等的发展权。觉醒的女性走上街头,童工法案遭遇抗议,残疾人工会争取权益——这些斗争本身就在缔造新世界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不留余力地支持这些运动的。
种族、民族、宗教
至于种族和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有以下见解:传统“人类种族”概念将人类划分为若干基于外貌特征的群体,但现代生物学研究已彻底否定了这一分类的合理性。从基因层面看,人类群体内部的遗传连续性远超离散性,根本不存在符合生物学定义的“种族”界限。人类基因组计划揭示,全体人类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9.9%。所谓种族间的基因差异,仅占人类整体遗传变异的0.1%。这些差异中,85%存在于所谓“同一种族”的个体之间,仅15%分布于不同地理群体间。肤色、发质等表型特征由极少数基因控制(约0.01%的基因组),无法反映遗传全貌。而被视为种族标志的肤色差异,实为紫外线辐射梯度下的自然选择结果:高纬度人群浅肤色促进维生素D合成,赤道地区深肤色预防叶酸分解。类似的血红蛋白变异(镰刀型细胞)、乳糖耐受性等适应性特征,其地理分布与传统种族划分完全错位。
群体遗传学数据显示,人类遗传多样性呈现渐进式地理梯度变化,而非跳跃式断裂。非洲大陆内部基因多样性超过其他大洲总和,证明现代人走出非洲后的奠基者效应导致遗传多样性递减。将这种连续性变异强行划分为“黑人”“白人”“黄种人”,如同将彩虹切割为若干色块般武断。种族概念本质上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其分类标准随历史语境变动(如美国“一滴血原则”)。基因组宽泛关联研究(GWAS)证实,自称同种族群体的基因异质性,往往大于不同“种族”间的平均差异。2019年《科学》杂志的多中心研究显示,基于基因型预测个体外貌特征的准确率,远高于预测其自我认同种族的概率。
现代生物学证实,人类是遗传多样性最低的物种之一。坚持种族分类不仅违背科学事实,更延续着殖民时代的认知遗产。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而非虚构的生物差异。正如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卢旺汀所言:“人类种族的生物学概念,已死在二十世纪的科学进程中。”
同时,民族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种分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达到顶峰,催生了现代民族的两个核心要素:统一市场和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割据,形成全国性商品市场,使原本分散的地区性经济整合为统一经济实体。蒸汽机与印刷术的发明,推动共同语言标准化;铁路网与关税同盟的建立,消除地域壁垒。正如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强调,民族国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组织形式”,其形成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同步发展。民族本质上是特定历史阶段中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其内核是人民基于共同生存境遇、文化传统及对压迫结构的反抗意识所凝聚的阶级利益联合体。当群体在反抗殖民统治、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本异化的斗争中形成集体政治身份时,不论其是否完全符合语言、地域等外在标准,都应被承认为民族。越南在抗法斗争中整合的多元族群意识、巴斯克人在佛朗哥独裁时期强化民族认同,均证明政治实践而非固定特征才是民族建构的核心动力。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前资本主义社会仅存在原始民族(Stamm)的胚胎形态。以西欧封建社会为例,农民对领主的效忠超越地域认同,教会拉丁语压制方言发展,地方性集市无法形成经济共同体。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本质上是文化认同而非现代民族意识,士大夫阶层通过科举形成的官僚集团,与群众存在根本性文化断裂。可见,前资本主义的人民所忠诚的对象不是国家本身,而是皇室、领主、城镇、地方或行会。人们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英国人、中国人等,而是城镇或城市的人。
与此同时,宗教矛盾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延续,在民族建构过程中被统治阶级有选择性地工具化。封建领主通过将宗教教义与血统论结合,塑造“神选民族”的虚幻共同体,如中世纪欧洲君权神授论将法兰克人渲染为“新以色列人”,以此合理化对异教族群的征伐。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在资本主义时代演变为更隐蔽的异化策略: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宪法层面确立“宗教自由”原则,另一方面通过资本操控媒体建构“宗教-民族”绑定叙事,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教派冲突。2020年开江县长岭镇的民族宗教矛盾排查报告显示,84.6%的涉宗纠纷实质是资源分配失衡引发的经济利益冲突,却被异化为“信仰尊严受损”的表象。
此外,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揭露,资产阶级通过将宗教矛盾升格为“民族宿怨”,成功掩盖了德意志银行家与犹太高利贷者共同剥削工人阶级的事实。到了现代,美国福音派又将新自由主义包装为“上帝旨意”,使南方白人劳工将对跨国资本的不满扭曲为对穆斯林移民的仇恨;以色列当局利用犹太教正统派教义,将巴勒斯坦土地侵占美化为“应许之地”的宗教使命。2023年金安区横塘岗乡调处的寺庙边界纠纷案例证明,当资本介入宗教场所商业化开发时,信仰差异立即成为争夺香火经济利益的动员工具。
可见,晚期资本主义通过制造“消费-信仰”的虚假需求,使有宗教特色的认证标识成为各种跨国巨头开拓各种市场的新型剥削工具,完成从精神异化到经济榨取的全链条控制。
近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包括:基于商品交换的有机经济联系、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标准化的国民教育制度。而这些要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缺失,这证明了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外壳。这里补充一下:美国联邦制看似分权,实则通过宪法框架构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核心集权机制。1787年制宪会议确立的联邦权力体系,本质是汉密尔顿等工商业资产阶级为打破州际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度量衡、镇压谢斯起义等民众反抗而设计的制度。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使中央获得最终裁决权,形成“分权表象下的法律集权”。1913年美联储体系建立,使货币发行权彻底中央化。各州无权发行货币,联邦政府通过国债和税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宪法明文规定外交与国防专属联邦,各州国民警卫队战时自动转为联邦军队(1916年《国防法》);宪法“州际贸易条款”赋予联邦调控全国经济的绝对权力,1937年最高法院对《全国劳工关系法》的认可,使联邦权力突破传统界限,直接介入劳资关系。历史证明,当阶级统治遭遇挑战时(如1967年底特律种族暴动),联邦政府立即启动《叛乱法案》实施军事集权。这种“危机集权机制”恰恰暴露了联邦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日常维持分权假象,危急时刻显露集权獠牙。
当然,《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工人没有祖国”并非否定民族存在,而是揭示民族国家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通过民族主义达成三重统治:对外以民族利益包装殖民掠夺,对内以国家认同消解阶级矛盾,对工人以“同胞”概念模糊剥削关系。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解剖民族主义的双重性:被压迫民族的抗争具有进步性,但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包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素。1914年第二国际的破产,正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以“保卫祖国”为名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恶果。资本的国际流动决定工人阶级斗争必须超越民族疆界。民族主义分裂工人阶级的典型例证,可见于美国“排华法案”期间资本家挑动白人工人仇视华工,而这种策略成功将周工资从3美元压低至1.25美元。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揭示,英国工人工资水平与印度殖民地的剥削程度直接相关。现代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使不同国家工人的劳动过程成为同一剩余价值生产的环节。
生态保护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始终是动态的、实践性的物质交换过程。马克思强调,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构成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这种物质变换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物质转化为生存资料,确证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必然性”,即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制约。恩格斯在考察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古代文明衰落时发现,当人类为短期利益破坏自然系统的再生能力,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这种辩证认识打破了将人与自然割裂的形而上学思维,既反对将自然神化的生态浪漫主义,也批判将自然工具化的机械论观点。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被马克思视为制造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剖析,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物质代谢的断裂”:土地肥力被掠夺式开发,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割裂了物质循环链条,工业生产排放的废弃物超出自然净化能力。这种断裂的实质是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与自然有限承载能力之间的根本矛盾。资本将自然要素降格为商品,通过私有制将自然资源的公共属性转化为排他性占有,使森林、水源、空气都成为资本增殖的牺牲品。利润驱动的生产模式必然导致环境成本向劳动者和未来世代转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技术应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加剧了生态危机。马克思注意到,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使技术沦为剥削自然与劳动的双重工具:蒸汽机的普及加速了煤炭资源的枯竭,化学工业的发展污染了河流与空气。技术的选择并非基于生态合理性,而是服从于缩短资本周转时间、提高剩余价值率的需要。这种异化在殖民扩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资本主义通过暴力手段掠夺殖民地自然资源,建立全球范围的剥削体系,使生态危机突破地域限制演变为全球性问题。恩格斯警告说,对自然的统治必须转化为“对生产方式的调控和对产品的支配”,否则人类终将沦为自身创造物的奴隶。
马克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述具有鲜明的辩证特征。他既反对将自然抽象为供人任意攫取的资源库,也否定将人类降格为自然附庸的生态宿命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揭示出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同源性。真正的解放意味着人类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发展,这种发展既包括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也包含对社会关系的改造。
当前全球生态危机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预见性。资本全球化导致的热带雨林消失、海洋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碳交易、生态税等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但这不过是资本对自然进行金融化掠夺的新形态。真正的生态保护必须突破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在重建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恢复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既需要技术创新提供物质支撑,更需要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来保证生态理性的优先地位。马克思留给当代的启示在于:生态问题的解决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命题,其最终解决必须通过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
实现生态解放的根本路径在于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全面异化,只有建立“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调节社会生产的制度,才能重建“人类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共产主义社会通过消除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生产既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又适应自然系统的再生规律,从而在生产力层面发展循环经济,使废弃物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在生产关系层面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环境剥削的阶级基础;在意识形态层面培育尊重自然的文化自觉,克服消费主义对生态价值的扭曲。
(4)作为反压迫实践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者100%地赞成女性、各被压迫民族、儿童、老人、残疾人的彻底解放,对此没有丝毫的犹豫、模棱两可或怀疑。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打击对女性、被压迫民族的压迫,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在任何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允许这样一种印象存在,即在某种程度上把“身份政治”当作一个可以归入阶级斗争一般范畴的次要问题。如果这些被压迫群体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准备将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斗争推迟到社会主义胜利之后,这对马克思主义事业将是致命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扭曲。
诚然,女性(和男性)、各民族、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完全解放只能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实现,这样的社会只能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来实现。但是不能指望这些被压迫群体将他们迫在眉睫的要求置之不理,干等着社会主义的到来。如果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天为进步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平权,而不是特权;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身份融入一般生活,而不支持把身份当作一个炫耀的、为自己谋取特权的原因。(假设你是一个同性恋,那么你就不会到处宣传你是同性恋,同时穿的另类来表示自己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任何性取向都和异性恋一样是正常现象,有谁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异性恋而奇装异服,并无时不刻地和别人谈论自己的性取向呢?)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争取哪怕最微小的改良,以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原因有两个:1.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保卫工人免受剥削而斗争,捍卫生活水平、民主权利和文化生活的最基本条件,捍卫文化和文明免受野蛮的侵害;2.只有通过日常斗争的经验,工人阶级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组织力量,把集体意识提高到历史所要求的水平,以促进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
我们举个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问题看法的例子: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被压迫民族通过革命性自决摆脱殖民统治或前资本主义的压迫,但反对资产阶级利用民族主义分裂个人阶级国际团结。列宁指出,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必须承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但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力量不应将分离作为最终目标,而应促成各民族劳动者联合。当民族分离运动被反动阶级操控、破坏工人阶级整体利益时(如崩得主义试图用民族文化割裂阶级阵线),对其进行批判和纠正属于革命需要;但若一个政权以暴力强制同化、剥夺民族平等权利(如沙俄的民族压迫政策),则构成对自决权的践踏。关键在于是否服务于消灭阶级压迫:前者消除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革命的干扰,后者维护的是剥削阶级的民族特权。
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要求这些被压迫群体“为了革命的利益”搁置他们的日常要求,这种思想是愚昧之极的,这将使我们的斗争脱离现实且孤立无援。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革命将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的海市蜃楼。同样,坚持争取提高女性、被压迫民族、LGBTQ+等群体地位的斗争,争取进步的改革和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所有人类的完全平等,是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职责。
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有必要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或是民族主义者,或是生态主义者等具体身份才能与这些重要群体联系起来?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马克思主义里本身就包括这些内容。归根结底,所有问题(民族压迫问题、男女对立问题、恐同问题、环境问题等)都具有阶级性质。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所有其他反压迫斗争表现形式区分开来的基本分界线。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群众运动的经验的集中,因此它自然就包含所有的相关内容,而不需要特别强调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和这些群众解释清楚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是女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生态主义者等,同时告诉他们马克思主义包含什么、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