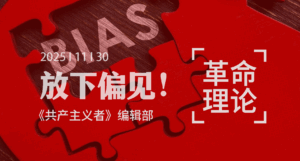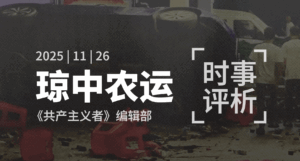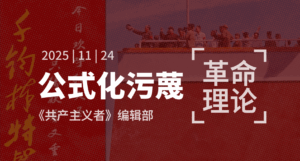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在探讨南亚印巴问题这一延宕至今的政治冲突时,必须超越表面的宗教或民族矛盾叙事,而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观进行全面分析。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政治目的、手段和结果等方面出发,剖析印巴问题的本质成因——印巴问题深刻揭露了“宗教意识形态”与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身份构建因帝国主义的煽风点火被彻底动员为阶级统治、瓦解工人阶级的工具。印巴问题遗留至今的腥风血雨恰恰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为可憎的遗产之一。
显然,任何能够认清基本事实的人,无论抱有何种意识形态,都明白英帝国主义在南亚的扩张绝不是其所宣称的“现代化使命”,而是赤裸裸的资本掠夺与过剩产品倾销。自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通过军事与商业手段控制孟加拉以来,英国统治者通过暴力镇压与制度控制,摧毁了全南亚次大陆的自给农业结构与手工业体系,使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地区被纳入帝国主义势力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之中,成为原料供给地与廉价劳动力市场。英帝国主义深知分化当地民众的重要性,其惯用手法即为通过法治、教育、宗教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再生产,认为创造当地民众的“身份认同”分裂,如锡克教和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宗教在被英帝国主义人为发明为所谓民族身份后互相之间产生的冲突,这一现象和巴尔干半岛波斯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被奥斯曼帝国通过种族屠杀与隔离的方式强行转化为穆斯林、发明“穆斯林族”的历史进程是如出一辙的。
作为历史迥异、文化差异巨大的上层建筑,宗教是帝国主义势力分化瓦解民众最好的武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宗教逐步从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组成要素,异化为政治动员的核心工具。英属印度在制度上确立了基于宗教的身份治理模式(这也是从奥斯曼帝国的米利特体系与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成分体系中习得,帝国主义势力向来是臭味相投的一丘之貉),将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耆那教徒等分别纳入不同的行政、教育、司法轨道之中,从而人为构建出两个“族群实体”,为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服务。在这一框架下,宗教不再是纯粹的信仰实践,而是用以分辨资源二次分配的标签。这一制度性的所谓“认同”分裂,为后来的印巴分治埋下了最为深远的结构性种子。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本身也并非一个单一的反帝国主义共同体。在帝国主义统治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受到了殖民资本的高度干涉,其发展依赖殖民经济的边缘环节(即南亚次大陆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此在政治上也依附于殖民势力治下的社会稳定。印度国大党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追求国家独立的同时,始终试图维持社会秩序与自身既得利益,对广大穆斯林小资产阶级与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诉求反应迟缓,导致同样寻求独立的穆斯林联盟逐步强化“两个民族”的政治主张。在这个过程中,穆斯林民族主义并非源于所谓宗教信仰的觉醒,而是穆斯林社会内部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国大党主导的泛印度民族主义中被政治边缘化所采取的反制对抗措施,代表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同国大党印度教资产阶级精英集团与英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这一矛盾不可弥合的背景下,1947年的“印巴分治”代表英帝国主义彻底放弃直接管理当地。印巴分治绝不代表去殖民化,而是帝国主义有组织、有目的地制造的地缘分裂,核心目的在于将已经被人为创造的民族矛盾激化点燃为持久冲突,从而维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南亚的间接控制。由蒙巴顿所主持的分治计划,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草率划界,不仅未解决民族自决问题,反而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超过1200万人口因宗教信仰被迫迁徙,造成百万人死亡,而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问题更成为分治留下的最大火药桶——这两个地区的当地民众为穆斯林主体,但是统治者为印度教地方土邦贵族,进而在领土分割时保留了“独立”,随后通过政府合并与民意统计作为支持分别被选成为新成立的印度共和国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领土。印巴分治过程中的大量无组织暴力不仅是民族矛盾,更是殖民主义推波助澜的直接后果,也是新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独立时因极为复杂的阶级矛盾集中爆发的后果。
分治后,印度与巴基斯坦分别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构建方法,然而南亚次大陆从未逃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干涉与内部统治阶级和社会阶层错综复杂的势力网络。印度在继承了殖民行政机器的基础上,确立了表面上的世俗宪政体制,但其实质上却是在印度教多数主义基础上维持通过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维护政治稳定,并长期边缘化穆斯林、达利特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而在经济政策上,印度虽然在初期推行形式上的国有化与计划经济,但其从未能够真正实现土地改革或消灭生产过剩,反而使城市中产阶级在精英官僚集团执掌的国家体制中获得特权地位,形成印度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巴基斯坦则更为明显地将国家认同与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绑定,试图通过宗教统一来弥合内部民族矛盾。然而,俾路支、信德、普什图等族群与旁遮普人之间的民族差异与阶级状况的巨大分化无法被单一宗教所消解,这些地区的人民也普遍反感伊斯兰堡或白沙瓦地方寡头带来的经济剥削。1971年孟加拉(原东巴基斯坦)的独立,正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统一失败的最清晰体现——显然,同样没能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经济自立,同时面对外部帝国主义殖民与中央对地方经济内殖民的巴基斯坦无法有效处理任何内部的阶级矛盾。
冷战期间,南亚次大陆也充当两大阵营的第一前线。印度与苏联结盟,巴基斯坦成为美国的盟友,而克什米尔问题则成为武装对峙的焦点。随着1998年印巴两国相继进行核试验,南亚次大陆开始了核威慑时代。在核威慑之下,两国不再进行大规模武装冲突,而是先后使用恐怖主义、边境骚扰等各类手段试图通过蚕食战略扩大自身利益,进而导致地区局势长期升温。在今年,两国还使用了空袭等新时代战争中常用的低烈度攻击手段作为测试对方底线、争夺利益和政治话语权的方法。
十分明确的是,南亚次大陆的根本问题在于,印巴两国无论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产生还是政府的治理体系,都始终未能脱离殖民资本主义的遗产,其甚至不能算得上是充分现代化的独立资本主义国家。印巴两国所谓的现代化与去殖民化长期维持对各类无产阶级民众的剥削,通过殖民时代整个南亚次大陆内部以政治和经济中心(如德里、加尔各答、卡拉奇)对其他劳动力密集区域的经济压迫和剥削维持国家权力。在这国家体系中,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对全体“他者”的排斥,无论是在国内外都通过各类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转移内部阶级矛盾,制造各种民粹主义的政治幻想。在印度,这种机制体现为“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政治崛起,将穆斯林群体妖魔化以维持印度统一的合法性;在巴基斯坦,则体现为军事建制的常态化,以“国家安全”名义压制民主和经济进步、反压迫诉求,维持对边疆和西北山地地区的控制,进而形成一个军阀国家。
因此,印巴问题的实质并非两国民族之间无法和解的宗教仇恨,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去殖民化失败血淋淋的教训,是殖民秩序局部解体后无产阶级未能被动员起来打碎旧有国家机器、建设新政权的一场悲剧。宗教、民族、领土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被政治化、制度化,成为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工具。如此,克什米尔不是简单的“争议地区”,而是帝国主义维持军事撤退后持久经济利益的牺牲品,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帝国主义战略性收缩夺得不完整喘息空间的畸形儿。唯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碎一切殖民时代所遗留的国家机器,方能还南亚一片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