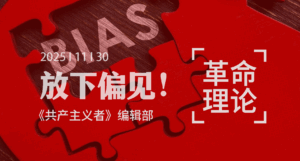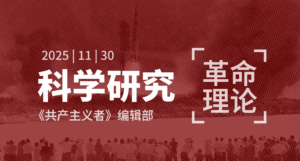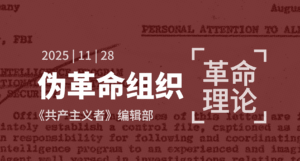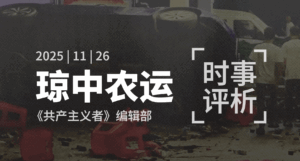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谈到性少数,很多天天喊解放无比大声的共产主义者就突然闭上了嘴;中国对于性少数整体保守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一方面担心“倾向”性少数会让自己挨骂失去支持,一方面在这个环境中收到了很多影响,导致自己个人对性少数的态度悄悄地操控政治立场。
伪君子们平日说要“为所有人争取解放”,而到了真该证明自己时,就说,“哎呀,这个问题你不是不知道中国大多数人怎么想,我们对外宣传可不能那么说,性少数支持了名声就臭了。”这种最为机会主义式的立场,说白了就不是先锋队的立场,而是跟着群众的屁股走;革命者在他们眼里只需要顺从群众,即使是群众思想不足的地方,为了群众的支持他们也要昧着良心陪统治阶级一起骗群众,来谋求短期那虚幻的“群众基础”。
对群众宣传的手段,的确需要看客观的环境灵活选择;但一个革命组织的立场,可不能每天一变、言而无信,更不能为了博取无产阶级一部分的支持,助长我们阶级的内斗去反对无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对性少数问题,那些用“中国保守文化”作为借口的懦夫,要不是嘴上一套(装成这样不然被其他革命者骂反动)实际心中就是倾向反动派的立场,要不就是不谋求提升工人阶级的觉悟和阶级意识,只愿意在当下工人阶级的思想水平上做应和的工作。这就和很多台湾左翼说,青年都支持台独,那我们宣传上不能犯傻,也要“批判性支持”,最后给自己的统治阶级打工一样。
对性少数不能不谈。资本主义压迫性少数,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在今天宣传“觉醒”的所谓的“民主国家”,几十年前他们的嘴脸还是另一幅模样:20世纪初期英国将同性恋视为犯罪行为,最著名的例子是数学家艾伦·图灵,他因同性恋行为被判刑,并被迫进行了“化学阉割”;纳粹政权将同性恋和跨性别者被视为“不道德”或“堕落”的象征,并将许多人送往集中营。虽然在战败后废除了诸多纳粹时期的法律,但直到1970年代,西德才彻底解除了对同性恋行为的禁令;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高潮时期,参议员麦卡锡视同性恋和共产主义称为“对美式生活方式的威胁,而同性恋和共产主义二者与疾病和瘟疫的联系,为隔离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同性恋也被与国家安全问题挂上了钩,因性取向而被解雇的政府官员数超过了因秉持左翼或共产主义思想而被解雇的官员数。但是问题是,资本主义压迫性少数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
是单纯的“文化道德的传统”吗?这是否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所谓的完善和进步来消除这种压迫呢?性少数群体被资本主义压迫的原因并非单纯的“思想保守”这么简单,这是统治阶级用于遮掩真相的外衣。我们首先要先理解今天“性少数”群体以及这整个概念的历史与根基。
性少数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的存在的历史同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长。在原始文明中都曾广泛存在着“第三性别”,例如,在底比斯附近发现的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陶器碎片展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类性别:男性、女性和sekhet。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冒险家也指出,在加利福尼亚原住民中,“有一类印第安男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更远的内陆,都身着女人的服装并有着女人的性格”,他们“以通奸为职业”而且“备受推崇”。在《史记·世家·魏世家》中也曾记载过跨性别的存在:“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但是,性少数真正拥有身份意识并作为一个自觉的群体出现却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古希腊、罗马或中世纪欧洲,虽然同性性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但它们并未发展出“同性恋”这一概念。这些行为通常被视为“某种行为”,而非“某种身份”。而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性少数群体开始产生身份意识。当代工业社会为男人和女人创造了认同自己并以同性恋身份生活的可能性,我们所说的“同性恋”,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里,并不被认为是一套统一的行为,更不被认为是一套定义特定人的品质。是现代资本主义将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卷入到了社会“角色”和态度之中。
事实上,是资本主义为人们创造了基于个人欲望“性少数”群体身份形成的社会和物质条件,这是对曾经包办婚姻的封建教会和社会权力的历史性突破。在封建社会中,家庭不仅是生殖单位,也是生产单位,例如一直占中国古代经济统治地位的那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欧洲14世纪以后出现的庄园经济,这种封建小农经济使得人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仅限于自己家庭周围。除此以外,还有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地主利用各种手段将农民束缚在田地里。总而言之,人们的活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缺少信息交流。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晚期西欧和北美城市中心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兴起,雇佣劳动变得更加普遍,社会化大生产迅速发展,家庭与工作的分离程度越来越高,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人们不再依赖家庭,而是依靠工资劳动谋生,这带就导致了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进入城市,在工厂或商业机构工作,不再依赖于家族土地或家族企业。工业化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使得人们不再受限于小型农村社区的道德监督,可以在更自由的环境中探索个人身份。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个人被视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个性和个人选择的概念得到强化。这些为LGBT身份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使得非传统的性关系在城市里更容易发展,并形成了特定的社群和亚文化。例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的大城市如伦敦、柏林、巴黎和纽约,出现了同性恋酒吧、俱乐部和社交圈。这些空间使得同性恋者可以聚集在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性少数群体,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这并不是说性少数行为是资本主义创造的,而是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性少数”这种身份认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清宣传所谓“性少数”是一种疾病的保守派是对于科学和历史多么的无知,以及今日身份证治的支持者理论上的空洞。性少数不是一种病,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个团体,而是在近代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社会和物质改变推进形成的一种身份认同。那为什么资本主义要对这种自己创造出的身份认同如此防备呢?
那是因为性少数群体的存在挑战了资本主义根基上依赖的传统家庭。传统家庭是私有制社会的社会细胞,在其中家庭内,男子是家庭中的“资产阶级”,而女子则是家庭里的“无产阶级”。男子掌握家庭中的物质财富或者生产资料,家庭的经济来源基本依靠男子的劳动,而女子则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这便是性别分工。马克思曾指出:“分工和私有财产是相同的表述:一个表述是关于活动而确认的,另一个表述是关于活动产品而确认的。”在私有制社会里,家务劳动是私人劳动而非社会劳动,女子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以外,这就是说,女子在经济地位上是依附于男子的。正如奥古斯特•倍倍尔同志所说:“一切社会的从属和压迫是起因于被压迫的经济的从属。”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要进行再生产,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其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十分重要。
尽管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后,已经极大的削弱了父权制家庭,使得我们能看到今天的传统家庭不像往日一样只有男性在外工作,但由于其需要大量的、不断生产的工人阶级来维持生产,所以保留了部分传统家庭的核心内容。尽管现在女性早已参与了社会劳动,但女性在核心家庭中的角色依旧被限定为“母亲”和“照顾者”,她们依旧需要承担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责任,这就使得资本主义体系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劳动力。这一过程并不需要资本家支付成本,而是通过家庭结构将育儿负担转嫁给女性和家庭,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可以得到无成本的劳动力,性别分工为资产阶级带来了物质利益。
家庭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她的“无形”劳动价值被资产阶级所占有,并通过她在家庭中的角色为资产阶级带来利益,这就要求她购买食物、衣服等,做饭,维护家庭,照顾家庭,包括各种情感和心理需求,如化解丈夫因工作剥削而产生的愤怒。 因此,尽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法律上宣传“男女平等”,但在就业中依旧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同时,家庭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通过不断给无产阶级的子女后代灌输符合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的意识形态,从思想文化方面保障劳动力再生产。为了维持对其统治至关重要的劳动分工,资产阶级形成了一种强大而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渗透到教育和文化中的截然相反的性别模式:男人要身强力壮、勇敢善战;女人要学会支持和被动。从童年开始,男孩(汽车、机械装置、枪支)和女孩(洋娃娃、缝纫工具包、游戏炉)都要接受玩具的训练,以适应他们最终在经济中的角色。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确保这种灌输贯穿人的一生。
而性少数的存在却挑战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家庭。性少数家庭里蕴藏着性别平等的萌芽,在男女同性恋家庭里,没有抚养后代的需要,所以同性恋婚姻里的双方都可以参与社会劳动。而且由于婚姻双方性别相同,没有生理上的差异,所以他们往往共同承担家务劳动。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隐含着对将关系建立在根据身体特征基础上的必要性的否定。当男女都认自己是平等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失去了“分而治之”的基本武器之一。所以,在同性恋家庭里不存在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情况,这就挑战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双方不平等”的思想。并且由于性少数家庭基本没有进行生育的条件,无法为资产阶级提供不需要成本的劳动力,不符合资本增值的需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性少数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如今世界各国普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尖锐。中国资产阶级政府面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危机,对女性和性少数展开了迫害,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政府试图将女性重新塑造成“生育和家庭责任的承担者”,在三孩政策出台后,政府宣传开始强调“女性生育义务”,通过各种渠道塑造“多子多福”、“女性天职”等观念。例如河南、湖南等地的宣传标语,如“生娃是家事,更是国事”或“妇女是民族未来的希望”,还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打压追求女性权益的声音,企图让女性重新回到家庭。
而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开展了对性少数群体的迫害。它在全国各地大兴所谓“戒网瘾学校”和“扭转机构”等集中营,企图用暴力的手段扭转性少数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还给性少数群体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将他们关押在精神病院中,更是企图通过社交媒体等宣传机器对性少数群体的声音进行封杀。例如2021年7月,中国各高校的LGBTQ+学生社团公众号被集体封禁,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性少数社群。2018年,广州的“同语”机构被迫关闭,而该组织曾致力于反歧视法律援助和艾滋病防治。
性少数群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仅仅是所谓文化道德的“进步”或者“保守”,而是性少数群体的存在威胁到了资本主义赖以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家庭,挑战了几千年来私有制社会家庭里婚姻双方不平等的制度。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对性少数的压迫绝不仅是因为他们“思想保守”而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必然要求,是具有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物质利益对性少数的有意压迫。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歧视和镇压引起了性少数的自发抵抗。石墙酒吧位于纽约市格林尼治村,是当时的LGBTQ+社区聚集地之一。当时的美国警察经常会突袭同性恋酒吧,进行骚扰、逮捕并羞辱顾客。石墙酒吧也不例外,长期以来,它是警方频繁突袭的目标。 1969年6月28日凌晨,警方再次突袭了石墙酒吧,试图抓捕在场的同性恋者。不同以往的是,这一次酒吧中的顾客并未选择默默忍受,而是开始反抗。这一反抗迅速升级为暴动,酒吧外的街道上爆发了群众的抗议行动。民众不仅仅是为了抵抗警察暴行而站出来,也是为了反对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压迫和不公。这场暴动标志着美国同性恋者的反抗和自我解放运动的开始,也被视为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
现如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部分性少数的权利,例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跨性别可以更改证件性别等等。但这可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青天大老爷大发慈悲的“恩赐”,而是性少数群体通过长时间的流血斗争得来的。例如在英国的1970年代至1990年代,跨性别者通过法律诉讼、街头抗议、社群动员等方式进行斗争。最终,在2004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性别承认法》,允许跨性别者合法更改性别身份,这是欧洲最早承认跨性别者权利的法律之一。 不过,资产阶级对性少数权利的承认也不过是在一些“象征性权利”上的退让罢了。例如,每年6月,耐克、星巴克、可口可乐等大企业都会在社交媒体上换上彩虹标志,推出“LGBTQ+友好”产品。但他们却丝毫没有给企业内的性少数工人该有的福利待遇,没有消除职场中对性少数的歧视和限制。迪士尼公开宣称支持LGBTQ+权利,但被曝光向美国佛罗里达州“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支持者提供竞选资金。一边声称自己支持性少数运动,一边残酷压榨和剥削性少数无产阶级。
2021年,拜登政府宣布恢复跨性别者参军权利,宣称支持LGBTQ+群体。但美国跨性别者的贫困率高达29%(远高于普通人口),政府并未出台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跨性别者仍然面临高失业率、医疗歧视、无家可归等问题。很显然,资产阶级只关心他们能否去为帝国主义战争当炮灰,根本不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
这就可以解答困扰很多革命者的疑惑:为什么我看今天资本主义不是在镇压性少数,而是宣传性少数,搞出些离谱、反动的身份政治呢?那是因为,面对性少数群体的反抗,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再采用从前那种露骨的暴力手段了,于是“扛着彩虹旗反彩虹旗”成为了资产阶级应对性少数运动的新对策。 我们所熟知的“政治正确”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篡夺性少数运动领导权的产物。
一方面,资产阶级假惺惺地承认性少数的权利,另一方面在背地里通过各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打击性少数运动。 在组织上,资产阶级主要是通过收买性少数运动中的“性少数贵族”、或者让资产阶级中的性少数来领导性少数运动等办法来篡夺领导权的,以阻止性少数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企图把性少数运动局限在改良主义的范围内。这在历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列宁早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就对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贵族这种反革命策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帝国主义通过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使得一部分工人阶级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待遇。这些工人,不同于一般的工人,他们在经济上享有更高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他们在阶级斗争中往往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同样的,这部分被收买的“性少数贵族”就会按照资产阶级老爷的命令来行事,制定不恰当的斗争策略、脱离广大无产阶级的斗争、仅仅提出改良主义的目标等等。
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宣传政治正确、丑化性少数形象,例如2024年法国奥运会的开幕式,将性少数群体的形象妖魔化,在国际上对性少数的声誉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资产阶级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在广大无产阶级的心目中败坏性少数群体的形象,使人民群众对性少数产生反感和恐惧,以此分裂工人阶级。他们挑动异性恋工人去反对同性恋工人,挑动顺性别工人去反对跨性别工人,制造性别议题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转移阶级斗争的矛盾,以防止同性恋工人和异性恋工人、顺性别工人和跨性别工人形成阶级团结。
这种手法在历史上也有先例,例如种族歧视问题,就是通过挑动白人工人去反对黑人工人、挑动美国工人去反对亚裔工人来达到转移阶级矛盾、让无产阶级陷入内斗和分裂的阴谋,所以,反对团结性少数无产阶级群体的人都有意无意地陷入到唯心主义和分裂主义中去了。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一直以来都流传着一些对性少数问题的错误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性少数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别多元化是唯心主义的。 那么,先来说说性少数到底是不是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吧。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性少数存在的时间同人类存在的时间差不多长,前面文章已经证明了在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都是存在性少数的。这里再举一个《宋史》中的跨性别例子:“宣和六年,都城有卖青果男子,孕而生子,酵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性少数早已在古代社会中有所记载,而古代社会又只有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性少数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不攻自破了。为什么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性少数群体开展了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为什么性少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普遍遭受歧视和暴力?虽然性少数本身并不是“进步”的,但性少数群体却和资本主义有着不合调和的矛盾,这在上文已经论述过了。
性少数的生存状况远比顺直要恶劣的多,是不可忽视的现实。“性少数的平均教育程度略低于非少数。性少数中达到大学本科教育程度的比例为49.4%,略低于非少数52.0%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性少数肄业、退学或辍学的比例高于非少数,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他们获得更高教育的机会。而且,在性少数群体之间,间性人和跨性别者因其性少数身份在学业上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最大,肄业、退学或辍学的比例在20%以上。”(来自 联合国开发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数据收集期间受访样本失业率为11.87%,而同期由人社部公布的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3.97%。
那么,多元性别是唯心主义的吗?很显然并不是,多元性别并不是人们随意虚构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它和人类存在的历史差不多久远。就算我们先不考虑性少数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止存在两种性别。例如我所熟知的天生的双性人“扶她”,既拥有男性的器官又拥有女性的器官,那么请问扶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再比如说,正常的男性通常只有一个X和一个Y染色体。而克氏症候群患者有两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患者可通常会出现一些女性化特征,如较大的乳腺发育,以及更少的体毛。那么请问,可是症候群患者又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因此,否认多元性别才是真正的“性唯心主义”。这和之前网络上流传的美帝声称一共有九十多种性别同理,就是属于凭空捏造和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
所以,性少数是人类的正常现象,它和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长,它即不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就像黑皮肤也同样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一样。马克思主义与性少数解放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党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奥古斯特·倍倍尔是最早在公开辩论中支持同性恋权利的政治家之一,他在科学人道委员会旨在推翻德国刑事法第175条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沙皇政权迫害同性恋的法律,同性性行为在革命的苏维埃俄国是合法的,在这一议题上,苏俄成为当时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之一。当时在英国和美国,同性恋者仍遭受羁押,但是在俄国,男女同性恋都可以公开地和伴侣生活在一起。然而好景不长,1934年3月,斯大林在全苏联范围内,再次将同性恋刑罪化。后来整个苏联官僚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歪曲和整个联盟解体的现实就摆在面前:共产主义者说性少数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挖自己的墙角。
我们必须夺取性少数运动的领导权与话语权,而不是觉得这是什么“不纯洁的共产主义运动”任由其被资产阶级的支持者挟持。我们必须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在组织起自己时建立专门负责领导性少数解放运动的组织,就像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妇联一样,制定和宣传党的性少数政策,与群众中的保守思想作斗争,耐心解释让他们看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如同我们对沙文主义的宣传一样;我们还要坚决揭露性少数群体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领导层的伪善。一方面,我们要尽力为性少数群体争取一些有利的政策,例如医疗服务、反歧视法规等等。另一方面,要领导性少数群体与资本主义作斗争,与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结合,为推翻资本主义做努力。
共产主义将会是所有人的解放,一个人也不会被落下。放下资产阶级灌输给我们的谎言,无论他是保守主义式的还是身份证治式的妖魔化性少数,我们都要清楚的看出来:划分我们的不是性取向。资产阶级自由派鼓吹的身份政治,从来没有帮助性少数,而是将少数完全不代表此群体的贵族推上风口浪尖,吸引性多数的群众向性少数释放火力,自己则隔岸观火。性少数不需要“觉醒”给他们虚假的特权,而是要取得和其他劳动者与被压迫者一样成为自己劳动成果的主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自由选择如何被压迫的权力。
不管同志个人对性少数是什么印象,同志个人是否为性少数,这不该影响我们的判断,改变我们的政治立场。性少数的解放不是胁迫任何人去喜欢他、去接受他;我们的政治立场应该基于我们的阶级分析,而不是文化态度或者个人经历。
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不是由他或她的性取向或者性别来决定的,而是由他或她对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来决定的。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不在意你性取向是什么。我们在意的是,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组织起来,用最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为所有人带来一个平等、自由的新世界,你是否愿意奉献自己来为劳动者和所有被压迫者争取最彻底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