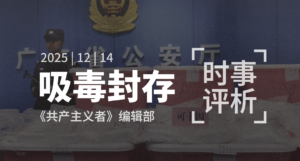作者:梧叶

12月13日是“国家公祭日”,中共会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仪式以纪念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在庄严的气氛下,大多数人对其的了解,除了三十万的人数与日军的残暴之外,似乎就没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影视的宣传或许还会在这一认识上添加日军的新闻战、安全区等等。事件本身被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宣传着:被侵略者与侵略者、无辜与恶意、人民与军国主义、手无寸铁与长枪大炮、中国与日本。对历史的建构总是指向当下;不过,先让我们看看历史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样我们便能更好地了解它如何为现实服务。
面目模糊的大屠杀
不过,先需要声明:我们准备在考察的过程中,暂且搁置道德因素对考察本身的影响,以免有人从道德的角度揣测我的意图。道德好像一条绷带,人们用它束缚住伤口,使得话语体系看起来更加自洽;但是当理性的解剖刀将伤口重新暴露出来时,我们才会发现,这条绷带完全没有促进伤口的愈合,只是遮住了伤口而已。伤口一经暴露,老旧的绷带本身就显得多余而无用,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解决病痛的药,而不是自欺欺人。
通行的南京大屠杀叙事中,都会强调日军的残暴。不过,如果了解过南京安全区创立的始末,就会知道,之所以曾经有建立安全区以保障平民安全的构想,是因为曾经设立过上海安全区,并且相对成功地运行了。那么,我们就能说日军在上海时就不残暴,到了南京就残暴吗?无论从国际法还是当时的道德准则来看,日军的行为都称得上残暴,但是如果因此就对日军进行标签化地描述,那么在思维上就是懒惰的,并且会陷入这样一个危险的陷阱:认为某些群体好像“天生地”就在道德上带有负面的因素,甚至直接就认为其“本质”就是邪恶的。但事实上,这类想法往往就是众多屠杀事件在思想上的源头。这种说法除了能够快速理解之外一无是处。

为了避免掉进这个陷进,左派人士谈及历史上的大屠杀以及战争罪行时常常主张“把军国主义与群众区分开来”。但是这种逻辑也很容易被反驳:挥舞屠刀的人,在参军之前往往也属于“人民群众”;听闻南京陷落后,日本民间普遍自发地庆祝(当然民众是否确实得知了发生大规模屠杀存疑);日本国内的报纸甚至还以夸赞的口吻报道了杀人比赛,可见这种内容也不会激起大规模的反对。现在,这种逻辑又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人民群众”真的有那么纯洁吗?即使要说“人民群众被军国主义毒害了”,反对者也会缠着不放:怎么军国主义光“毒害”这一国的人民?可见,这种逻辑还是有不足,因为它最多充当一个口号,但是还不足够充当一个科学的结论,它还没有跳出道德评判的窠臼,只不过是在为“人民群众”“脱罪”而已;但仅仅从这个结论中不能得出任何有益的信息。
重新审视大屠杀,我们首先发现它至少需要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1)绝对的权力。这点已经由日军占领南京城达成了。(2)严密的组织。没有组织的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而军队恰恰是很严密的组织(虽然日军的军纪并不是很严明,但这不代表当时的南京是完全混乱的 ,许多文献都承认,南京大屠杀是明显的有组织的屠杀而不是单纯的士兵失控,否则不可能持续六周之久)。(3)屠杀者认为需要进行屠杀,在这里主要是为了使中国人感到恐惧、瓦解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不过就现实来看,它适得其反。
屠杀者如何成为屠杀者?在这里或需要指出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即执行大屠杀者实际上多是“正常人”,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甚至连纳粹的党卫军都适用于这一点,因为“不正常的人”反而有可能破坏组织。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曾进行著名的电击实验,发现只要有适当的引导,特别是在权威的命令下,人很可能会做出超出他们道德判断的事,因为他们认为责任不在自己而在权威。表现在日军身上,就是军官会要求下级进行“杀人训练”,去杀死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以此不断克服他们“动物性的同情”。此外,丸山真男还指出,日军的暴行还与日本社会特殊的道德观念相关:战前日本个人是被忽视的,天皇被视为“绝对价值”,个人只有对天皇实践“臣道”才能体现出价值。官僚制与这种绝对价值的结合导致压力与责任层层传导、转嫁,最终落到每个最底层人民的头上。他们要么“下克上”,但这种反抗在天皇观念的刻意引导下很难走向革命;要么就只能对“敌人”施以暴行以保证贯彻“皇道”了。日本统治阶级塑造的文化霸权中对中国人的系统性丑化与本质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华民族被视为低人一等的种族,这也增强了屠杀者的“正当性”,减少了他们的负罪感。
当然,迫于“道德”的因素,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些现实性的讨论很少曝光在公众视野下。中共大概只愿意让无产阶级相信,参与侵略与屠杀的日本人一定都是“人面兽心”,在本质上就把日本人非人化;这倒是和日本帝国把中国人称为“支那猪”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因此,我们还需要对当时的日本进行一个更全面的考察。
“分散”的帝国
关于中共宣传下日本形象的构建,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无论是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七七事变、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描述它的时候都会加上一个定语,“蓄谋已久”。这个词语用高度的凝练规避掉了战前日本社会的复杂性。对近代日本的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日本实际上形成了“双重外交”的态势,即军部与内阁的意志很多时候并不统一。无论对朝鲜的侵略、干涉内政的行为还是在中国侵略战争的最初发动,都和军部中下级军官的“独走”有关。由于理论上军部有直接向天皇上奏的权利,因此军部经常先斩后奏,以逼迫内阁同意它的战争计划。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在关东军把溥仪接到奉天后,甚至还没有确定即将成立的伪满洲国的国体是什么。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也是典型:当内阁还在讨论如何“限制冲突”以保证在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时,边境的军人已经踏入了国界的另一侧,悍然挑起了战争。
这个事实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战后责任认定的困难。相比于纳粹德国对自己行为目的、过程和目标有着明确认识与严格执行,日本在战争问题上则是混沌的,或许大多数的势力都在期望着战争,但对于是不是应当现在进行战争、应当在多大规模上进行战争、应当最终得到什么结果总是在相互争吵。结果,在战后审判时,相较于纳粹对责任的承担与自己行为正当性的辩护,日本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为自己是被“推着走”的。他们的最高领袖是天皇,任何正式的国家行动都会以天皇的名义进行;但天皇又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平时作出政治家的样子互相辩论,一到承担责任时又变成了“只是服从命令的官僚”。
可以做一个最粗略的划分:战前,日本的中央政府,除了军部,往往并不主张如此快地出兵;中下层军官和小资产阶级由于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则是战争的狂热支持者。战争爆发后,日本需要建立总体战体制,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近卫文麿受到纳粹德国启发,曾计划建立一个“一党一国”的“大政翼赞会”,以实现“同志式的结合”,达成“全体一致”,但是各方面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党、财阀、官僚、军部)并不因此就结束对立,结果不了了之。当时的日本想要进行总动员无法仅仅依靠一个代替议会的组织,而必须要依靠地方官僚和农村的“名望家”阶层(往往是地主等)。
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右派运动的零散性。战前日本是法西斯主义吗?事实上很难这么说。法西斯主义运动往往发生在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之后,法西斯党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无产者阶级的代表人”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又利好资产阶级。可是当时的日本几乎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左翼运动。日本共产党不断遭到检举与警察机构的破坏,连许多党员都转向了国家主义;作为工会党的社会民众党更是打出了“反共产主义”的旗号,在战争爆发后支持总体战体制。在许多右翼的意识中,工人阶级也是被极度轻视的,倒是有着极为浓厚的农本主义。民间运动还由于较为专制的社会体制不能经常扩大,必须在军部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但下层青年军官每一次试图政变都是加强了既有的政治势力的控制力。政府依旧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多方势力的大杂烩。这样,整个日本民间的右翼运动就变得五花八门,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趋势与可能性,最终也只是加强了政府的力量,延续了这个体制。
正如上文提到的,真正的左翼在日本战前的政治生态中是缺位的,日本共产党没有承担起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统一党内思想教育的任务,使得面对经济大危机的凋敝时,民众想要改变、想要行动起来时,甚至几乎没有左翼的可选项。他们有着模糊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反政府情绪,但统治阶级文化霸权的灌输却把他们的情绪导向了军国主义、“精神主义”(既拒斥物质文明,认为东洋精神才是最宝贵、最有价值、最值得争取的)的意识形态,并且也正如上文所说,完全没有达到改造日本的结果。总得看下来,天皇意识对民间运动有着极大的制约,因此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把反对天皇制作为一个中心任务,才能引导群众的情绪走向真正的革命。当日本的共产党决定放弃反对君主制时,也是日本左翼运动失败的一个标志。 我们知道,日本的无产阶级同样地也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同胞,可是他们却由于日本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走向了支持、至少是配合与默许战争,可见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重要性。

因此,假定日本全国是一个邪恶的“大本营”,一个步调一致的战争制造者,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近代日本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前现代的机构与思想,并拖着这些累赘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内政权取得了一席之地,再加上对外扩张政策符合其利益,几乎没有设想过进行彻底地资产阶级革命,从而一直与地主与官僚的势力同流合污。工人阶级由于共产党的虚弱并没有形成成气候的运动,使得右翼占据了民间的政治生态位。农民人数一直占据人口的一半以上,既是最大程度地保留着前现代特征的群体之一,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损害程度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的诉求在地主、政党、财阀、官僚那里都看不到,只能借着军部以曲折蜿蜒和被扭曲的形式表达出来:军部曾假惺惺地表达对补偿农村的支持,并以此获得了大量支持,取代政党成为政府真正的掌控者,并成为侵略政策最暴烈的执行者,成为社会危机以最坏方式解决的持刀人。
很明显,这一系列的历史过程以“蓄谋已久”来表述存在着很大问题,它忽视了日本内部的复杂性,把一个在人们意识之上以客观规律显露出来的历史进程说得像是一个人的主动的决定。很显然,这种说法仍旧是意图让人们从纯粹的道德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这么看,仅仅说“日本的人民群众是无罪的”也是肤浅的,这种说法也只是在道德的层面上主张自己的观点,从而只能是无力的回击。如果要提炼一个能成为口号的、足够简短的表述,我认为可以是“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没有完成应有的历史任务”。
南京大屠杀叙事与“战后时代”的虚妄
如果把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看作一种“义务”,那么显然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南京大屠杀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三十多年中几乎完全淡出了公众视野,偶尔几次提到也是为了批判美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在社会主义成为主流思想时,对民族主义思想的克制尚且是有可能的。
但到了80年代,思想的“放开”使得南京大屠杀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首先是民间的纪念运动和向日本索赔的运动,随着官方对这种运动的肯定乃至鼓励,南京大屠杀迅速在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诸多战争罪行中突出出来,并成为“国耻”之一。1985年,大屠杀纪念馆建成。有关从南京大屠杀中得出的启示,最多的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和平是好的、战争是不好的,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价值判断,但是它忘了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战争?是的,军国主义右翼对发动战争负有很大责任;但不是说几句“不要右翼”“反对战争”他们就会自动消失。因此,表面的珍爱和平实际上指向了对右翼的批评;但只是对日本的右翼的批评,因为中国一直被它自己塑造成“和平之邦”。这种意识深处的中国特殊论隐藏着分化不同国度的无产阶级的可能,并将口头的和平转换成实际上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对立与战争的可能。
这些纪念运动想要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就必须有一个前提:和平依靠宣扬和平的观念就可以保全。但即使战争是“不祥之器”,也有“不得已而用之”的时候。比如国与国之间的恐惧:以一战为例,当时双方最开始都还没有做好打欧洲大战的准备;但是一看到敌方进行了动员,为了防止自己被敌方击败,也必须进行动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两大集团之间的对立,最终走向全面的战争。战前日本也一直有“满蒙线就是生命线”的说法,日本统治阶层一看到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就会担心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受损,从而在地缘政治上落入不利的地位。在这里,要消除战争,最重要的不是“消除国家之间的‘误解’”,因为那事实上就是绥靖政策;产生战争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互相对立本身。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与自己的阶级统治,必须要有军队,而这种军事实力往往同时也是对外扩张的工具,其它国家侵略或者侵犯其利益的可能性又更进一步论证了保有常备军的合理性。要消除战争,最终必须消除国家与常备军。

国外一些学者也对南京大屠杀重新发掘,并将其称为二战三大惨案之一、“人类文明的污点”。这里蕴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好像战后时代这种污点越来越少了,至少是在“文明国家”“现代国家”越来越少了。他们把文明的过程看作同时也是暴力从社会生活中消除的过程,但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每当阶级斗争激烈到一定程度,暴力就会出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依旧在不断地以战争手段维护自己的全球利益。日本也并不因东京审判和修改宪法而完全消除了自己的反动性质,不仅仅是因为右翼的残留,还因为日本由一个半前现代半资本主义的国家转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在阶级社会。因此,要摒弃那种“二战是正义对邪恶的战争”的看法,如果说法西斯是邪恶,那么抵抗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称不上有多么“正义”。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也不只是来源于反对侵略,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战争的过程中带来了共产党对人民的组织与战后进行革命的力量准备。
战后世界绝不是什么战争逐渐走向消弭的世界,绝对不是什么所谓“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世界。现在全世界右翼势力抬头、中美帝国主义之间互相博弈、民族主义思想泛滥,这都是实际的可能导向战争的因素。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一天,只要无产者之间的相互分裂与仇视还存在一天,只要国家与常备军还存在一天,这种可能性就永远无法消除。关于那种浮在表面上的和平主义的谬误,可以参考这篇文章(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 – 共产主义者 )。因此,“愿世间和平”不是一群人在网络上发几条评论就能达成的,它需要我们作最现实的斗争,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回答所有隐藏着战争可能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做的远不止纪念死难者,还要建立最彻底的工人民主使得一个“集中所有权力”的情况不会发生;用无产阶级本身的武装反对所有试图发动战争乃至屠杀罪行的统治者;用无产阶级的组织与联合反对所有试图用民族仇恨分化无产阶级的野心家;用革命反对发动战争的反革命!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