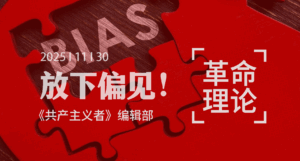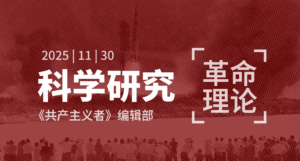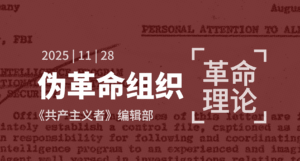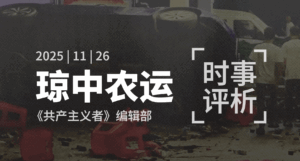作者:鼹鼠

里约热内卢在流血
2025年10月28日,里约州军警特种作战营 、 里约州警特种资源统筹局和里约民警在里约北区的佩尼亚与阿莱芒贫民窟发动了“遏制行动”(Operação Contenção),以打击上世纪巴西军事独裁时期由左翼政治犯在监狱中发展而来的城市游击队“红色司令部”,遏制其在贫民窟的势力扩张。当日行动警方动员约2500名警察,2架直升机、32辆装甲车、12辆工程车辆。 在十余小时的冲突后,巴西官方更新战果:缴获步枪逾90支、多枚爆炸物与大量毒品,记录逮捕百余人、其中数十人来自外州。至10月31日—11月初,多家机构的伤亡统计出现差异:州政府口径为121人死亡(含4名警察),公共辩护机构则称至少121—132人死亡,而警方的伤亡在宣传中被严重缩水,警察实际被击毙人数普遍估计为20人以上。

28日下午军警的突袭过程中,贫民窟内的多个帮派团体、武装民兵组织和红色司令部在多地展开反击。18点左右,红色司令部的成员开始在多个街口纵火焚烧轮胎,并起飞无人机对军警装甲车和警察局投弹轰炸。
晚间19点后,红色司令部成员占领了多个屋顶制高点,并压制了街头的警察部队。在贫民窟外围,红色司令部在各个交通要道和机场开始了大规模封锁行动,截止至20点几乎所有里约北区的关键桥梁公路都被红色司令部成员封锁,在里约全市造成了大范围交通拥堵。警方机动性被暂时限制的同时,红色司令部多个小队在米塞里科尔迪亚山脚的城镇进行阻击。
凌晨时分,警方重新集结力量后通过直升机投送的方式再次攻入贫民窟,在接连占领了多个重要街口之后成功与外围警队打通了交通线路。凌晨至第二天早上的时间段,警方几乎控制了贫民窟的街头,截止至本文撰写时间,红色司令部在卡罗比尼亚和贝尔福德罗克所等地开展游击战,并于11月5日在里奥博尼托伏击刺杀了一名PMERJ军官。此次冲突标志着本世纪仅次于巴以战争加沙战区的大规模高烈度城市游击战在里约热内卢爆发。
“红色司令部”与中国它“只说不做”的翻版
本次冲突中最亮眼的“红色司令部”源于上世纪70年代巴西监狱左翼政治犯结社,在早期通过绑架勒索官员富商和袭击警察局/军火库来获取资金和弹药。随着组织规模的逐渐扩大以及地下网络基本在全国城市贫民窟和农村等资产阶级统治的末梢建立起后,为了不激起政府的警惕和军警镇压,红色司令部逐步放弃了以往的游击战路线,不主动冲击政府/企业,转而利用自己庞大的行政和武装力量在巴西各地动员群众开展毒品种植/贸易。在垄断大半个巴西的毒品贸易的同时,红色司令部还热衷于投资文化娱乐,尤其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funk音乐。它在地上大量资助funk音乐创作者,制作有叛逆反抗内核的音乐来吸引年轻人参加音乐会,并在音乐会上向人群宣传组织、灌输理论、推销毒品,以此来招募新人并盈利。 红色司令部甚至与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和秘鲁多个游击队组成跨国地下网络:由地方领导小组和武装小队实际控制组织的生产和贸易运作,并以各地互保维系组织。
这样看,红色司令部的所做与中国互联网活跃的“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所提出的理论路线十分相似。引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在此基础上,地上组织和地下组织的力量大大发展,这时贫民窟的地下政权就随之建立了。它可以在地下秘密地逮捕和审判敌人。红色司令部可以持续派出武装力量,在政府统治薄弱的区域一边歼灭敌人一边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的势力范围,同时惩处敌人,巩固地下根据地的存在。在地下根据地,红色司令部有着绝对的优势。尽管企业照常开工,资产阶级政府依然在运作。”

巴西红色司令部不是一个力求动员、组织群众推翻政府的革命党,而是一个力求自身存活、用尽一切手段,甚至涉及黑产的军事组织。这就是中国马列毛大群幻想的宏伟大业只可能导致的结局。马列毛大群和红色司令部一样,将这种局限性辩解为“防守时期暂时的战术”。但是正如我们曾经在电台中指出:
“没有工人阶级或群众选择大批地加入到左派恐怖主义的行列中来,所谓的‘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也成了绝对的空头支票。”
换言之,“地下红军”的问题不是没做大,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大。巴西的例子已经是这一理论实践里的极限,得益于巴西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才得以勉强存活。就是如此,在这次警察的突袭中他们也只能做最后绝望的抵抗:政府有“反恐”、“扫毒”的正当性,有先进的装备、更强的武装力量和更灵活的全国动员能力,红色司令部则有什么呢?他们只有极少数战斗素质不如政府部队的民兵,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支持和群众的组织,更没有政治性的能将这一事件上升为一场革命的开始的思想。
中国他们的翻版更是好笑和无能。巴西“左翼革命者们”起码真正地建立起了一支武装力量,构建了地下的网络,垄断了毒品贸易。中国的“马列毛大群”除了其中精神不正常者在工厂里大吼大叫“发动罢工”、网络群组里在被罚钱的压力下写出一些意义不明的文章、在TG群组里闲聊外,没有更多的本事。他们的“地下红军”尽管可以和巴西进行类比,但存在一种本质性区别:他们只说不做。你不可能在“严格禁止线下、身边活动”的情况下建立武装力量、组织黑产,一群想东想西的学生和前政治犯能干出的事情,自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点上也不能责怪“马列毛大群”的成员无能,事实上以这种路线在中国做到巴西的规模,物质上就是彻底不可能的。如果要明白像红色司令部这样的帮派和民武的本质,我们就需要了解它们在巴西赖以生存的土壤——所谓“统治阶级的末梢”,非法地下活动最密集的,军警不占优势、行政力量鞭长莫及的地方——贫民窟。
贫民窟:“红色根据地”?
贫民窟是纯粹阶级压迫的产物。所谓贫民窟,并不只是收入低的人住的地方,而是被系统性排除在教育、医疗、就业与社会关系之外,是被剥夺了谋生路径的整整几代人生存的巢都——当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教育匮乏、医疗条件差、社会资源永远留给中产阶级子弟的环境中,这一个体被强迫面对的选择,是从一开始就被缩减到了零散打工的窄缝里,这种不稳定的低收入情况给了灰/黑产经济在贫民窟中发展的空间。我们看到的枪战、抢劫、街头毒品交易犯罪往往只是贫困人口中最显眼、最具戏剧性和暴力化的一小部分,而隐藏在背后的是大量剥削与掠夺。穷苦劳工被迫居住在基础设施崩溃的区域,房地产与贷款从破败的房屋和债务中榨取利润,企业把风险与不稳定全部丢给底层。在这种情况下赤贫并不是犯罪的原因,贫民窟青年之所以频繁出现在监狱名册上,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更邪恶,而是因为整个法律与治安体系被设计成通过监禁和枪杀他们来维持秩序。
而一旦当赤贫的无产阶级与犯罪被紧紧绑在一起之后,打击犯罪本身也成为镇压无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手段。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财政、规划与政策主动制造出贫民窟这种被隔离的空间,把劳动力集中封装在城市边缘,又能以治安、禁毒的名义持续向这些区域输出镇压、监控。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来说,贫民窟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一个可以源源不断生产敌人的空间。只要犯罪率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每一次扫荡和清剿就能在舆论上被包装成正义之举,成为选举动员、媒体宣传和军警机构扩张预算的正当理由。
红色司令部等帮派和民武组织正是寄生在这种绝望之上,它们的名称和口号看似激进,但实际上搞的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对于赤贫者来说唯一实际存在的上升通道与安全感。提供武器、工资、贷款与保护伞,用比国家更迅速粗暴的方式兑现秩序、就业和身份认同。所以,诸多像红色司令部那样的地下民兵武装与企业化帮派在主动利用无产阶级的穷苦本身来巩固统治。它们深知国家只在利益需要镇压时才进入贫民窟,因此有意填补那些被政府放弃或顾不到的缝隙,也就是所谓统治阶级的末梢(地下),去提供安保、仲裁和福利 也就是所谓“群众互助”,用赊账、施舍和暴力维系一种扭曲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所谓“基层夺权”。

在这种情况下,贫民窟的无产阶级们既是被剥削的,也是帮派和民武的人质,一旦有人试图脱离、或组织其他力量,他面临的是对整个家庭乃至整个社区的连坐报复。而它们所谓的地下根据地也是建立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供应链之上。红色司令部的组织结构中,真正的上游是军警、政府、买办——它们管理社会的基本运作和商品经济的流通,更具体的则是红色司令部销售的人脉;中游是分销、军火、赊账、高利贷等摧残人民的系统;下游是“安保费”、黑电黑水与交通线路的垄断“公有化”。每一项都能征到税,每一环都能从贫困里抽取现金流。所谓“红色司令部”等地下红军,在这种机制里更像是企业。它们打着革命的口号,实际在贫民窟对无产阶级直接的剥削和压迫甚至比美帝国主义还强,意识形态只是伪装,它们的底层逻辑仍是资本主义最血腥的一面,权力、利润、垄断与暴力。
我们也不能忽视了更大的历史与全球背景。像里约这样的城市并不是个例,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工的一部分。贫民窟中的黑帮贩毒等地下经济并不是与合法经济无关的黑暗角落,而是与银行洗钱、军火贸易、旅游业和房地产投机紧密勾连的其中一个节点。毒品利润和组织针对社区的税收最后总会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地下武装需要从合法与非法渠道购入武器,郊区、贫民窟的土地会被炒作成未来的基建项目。所以各方面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真正坚实的工业化“共产主义地下革命根据地”在目前这个高度流通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中根本就不可能在什么“统治阶级的末梢”诞生。
在红色司令部所谓的地下根据地里,孩子在枪声中长大,在毒品与武装的阴影下被迫早熟,在十几岁就被要求在为组织卖命和在无底的失业与饥饿里苟活之间做选择,无数人在其中挣扎,消磨,死亡。在巴西政府的镇压与红色司令部的“革命”战斗中,贫民窟百姓看见的,是一次次轰鸣的清剿,是装甲履带压过狭巷、无人机在屋顶投下爆炸物、亲朋好友被莫名其妙的拖出屋外乱枪打死在街头。军警撤退之后,“红军们”回到“根据地”,重建毒品制配室、割下所谓叛徒的头颅后把被扒了皮的尸体吊在路灯上、抓走无数孩童充军、继续层层加码地敛取费用;学校依旧缺师,诊所依旧无药,负债却比昨天更高,生存也更加没有希望。白天的屠杀与夜晚的混乱,像双轨并行的恶鬼:一条由国家演出,一条由地下红军经营,最终都把手伸向同一张地狱的餐桌。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