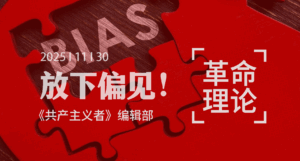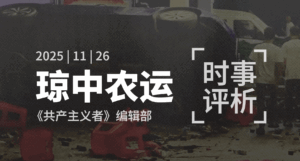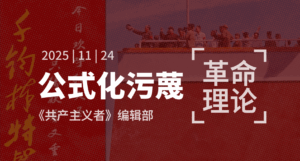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我就是全国第一个干这事的人,谁抬杠也没用!”最近,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类视频,他们说着这句话,宣布自己建成了一个“共享家园(山村/农庄/村庄……)”。其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王耀城。
对于王先生个人,我们其实没什么兴趣,毕竟他既不是第一个有办共享家园想法的人,也不是最成功的。诸如向前农场、小北回农村、水岸人家二庄主,办得比他早,至少到目前也在运营着。我们也不关心他个人的品质如何,不会无聊地把他办共享家园的事与他在此前卖珠宝的行为并列起来;强调他曾经帮人募捐、帮助抗洪也不会对我们的分析有所助益。
我们关心的,是他们的话术与所谓“共享家园”模式。
共享家园是如何经营的?
共享家园们很多都会如此宣称:他们要“打造六十年代的大集体”,吃饭、住宿、水电费,统统不花钱,一起劳动,一起共享,甚至还有民主权利。质疑声随之而来:吃饭不要钱?骗人的吧?会不会只是个噱头?其实共享家园这种经营模式,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如果真的把它当作“六十年代的大集体”,恐怕就有失偏颇。
首先,“六十年代的大集体”是在既有的农村实行集体化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本身就直接依靠历史上已经存在的物质基础。而共享家园模式是从零创建出来的,主要是利用一些弃置的土地、房屋等等资源,虽然降低了先期投资成本,但由于往往处于较为偏僻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预付地租等也需要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据这方面的博主宣称,仅先期投入就往往高达上百万。光是这笔资金,就决定了“共享家园”不是想建设就建设的,哪怕它真的是慈善项目,也必须依靠所谓“良心发现”的货币占有者才有可能建成,与工农大众的真实意愿无关。
其次,共享家园也不是慈善项目。我们看到,真正常住在共享家园的人数并不多,并且多是中老年人;规模也不算大,一个共享家园不一定比得上一个普通村落。其中人们从事的劳动,除了卫生劳动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业劳动(包括种植和养殖),但是我们几乎从未看过共享家园在这方面尝试过规模化、机械化地生产,反倒是为了宣扬所谓“回归农村”,我们见到的共享家园中的农业劳动几乎都是以手工为主。这不禁让人怀疑:与自然经济时期相差无几的劳动方式,真的能养活共享家园的居民吗?有的共享家园为了和居民打好关系,甚至专门用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农产品。钱究竟从哪来?
这就不得不提到共享家园中人们主要从事的另一劳动:服务劳动。这大锅饭不光是常住的居民吃,更多是前来参观的游客吃。有的共享家园选择对游客收费,这便是一笔收入,这种共享家园便类似于另类的农家乐。即使不对游客收费,也不意味着共享家园能够自给自足,它的收入还包括直播打赏、直播带货、短视频广告、付费课程(主要是自媒体课程、线下店铺引流等。也就是说,共享家园的经营非常依赖于互联网以及相关流量。否则,所谓共享家园一定会入不敷出。
共享家园是乌托邦吗?
即便如此,“免费吃免费住免费玩”的口号还是能吸引到不少人。一些是游客;另一些则是网左。对游客来说,把它当作一场低消费旅行的目的地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听信话术,真的把共享家园当成六十年代的大集体,便显得愚蠢了。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共享家园的经营本质上仍是一种商业模式而不是一个社会组织。它甚至不是“新和谐公社”那样的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它不过是个掺点泥的浪花。“共享”更多是博取流量的噱头,而不是一个改造社会的方针。因为这些创始人们根本没有一套成体系的理论,从来没有认真审视过,自己的这个家园究竟是什么,真正的共享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这个家园究竟如何才能存在。
可是,共享家园的诞生,需要货币所有者的投资;共享家园的存续,无论是承包费、水电费还是生活资料的购置,也需要依靠从网络平台中以各种形式取得的钱。在这里,“不花钱”以“花钱”为基础,并且以“花钱”的广泛存在为基础。再考虑到共享家园事实上存在的现金流,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不过是资本的又一形式;其中的成员是某种变相的员工。只不过它的盈利模式不仅仅是传统的靠卖出附有剩余价值的商品,还是利用共享的噱头来宣传。
这还涉及到中共的经济政策——乡村振兴。最理想的方案是在乡村搞出产业吸引就业人口,可是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时代这何其困难;于是很多地区便退而求其次,开展旅游业,打造“特色小镇”之类,吸引游客消费。这种模式往往与生产关系不大,生产在这里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存在那些有闲钱的游客。也就是说,乡村振兴最终走向了让“中产阶层”多消费,以这种扭曲的方式实行财富的再分配。共享家园事实上也是类似的思路。可是,随着经济下行逐渐严重、中产“破产”现象愈发普遍,中国本就不多的中产阶层更加缩水、更不愿消费,这条路也愈发困难,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很多跟风的“共享家园”大多难以维持。
此外,共享家园内部的民主也是一笔糊涂账。王耀城就是一个例子,他宣称“不会我一个人说了算”,可是整个共享家园的产权仍然在他手上;更别提什么民主制度设计了。事实上,在共享家园必须参与市场经济的时候,就决定了整个共享家园的运作仍需服务于市场,从而服务于商品生产逻辑,从而仍然是物的条件强制着人。
也就是说,“共享家园”不是乌托邦,它不过是资本想起的一个新点子,披上老旧褪色的军大衣。它本身就难以稳定,它依靠的也只是一个摇摇欲坠、极不稳定的社会现状。
“真正的”共享家园有成功的可能吗?
共享家园往往会宣称自己是一个世外桃源。王耀城的旗号是“乡村振兴”,四川向前农场的理念则是“田园生活”。他们都说,自己是在践行某种“理想”,显然,他们的话语与活动是非政治化的。共享在这里被解读为纯粹的经济活动,一如中共的宣传当中这个词的内涵。可是,一方面,共享家园的经济活动许多都在非共享的领域进行;另一方面,它从来没考虑过如何提高生产力,而只是在分配上下功夫。
假如我们发动空想之力,真的打造出一个大集体农庄,拥有现代化的农业设施、完全共享的经济制度、设计精妙的民主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了吗?仍旧不见得。马克思曾如此评价他们前辈拙劣的实验:
“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
首先,共享家园不可能与外界断绝联系。经济方面,它的先期投资本身就依赖于大量的货币;农业需要配套农具制造厂、化肥制造厂、粮仓等等,从而还需要钢铁冶炼、机械设计、原料生产、能源生产等等产业;生活方面也需要相关的配套设施。那么,整个共享家园就会需要一套工业体系,而这远非一个农庄能够建设的。那么,农庄就必须与外界有所交换,从而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政治方面,则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承认,但政府肯定不愿意看到一个封闭的、抱团取暖的社会组织出现。
其次,共享家园作为局部的改良性质的集体,其必然会遭到资本主义的抵制。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有大批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工人,资本通过不断地榨取剩余价值而维持这个前提条件。而共享家园的集体所有制则会破坏这一点,使得工人存在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可能性,这会造成劳动力的流失。因此,资本家们一意识到这种共享家园的威胁,即使它本身不瓦解,资本家们也会想方设法从外部摧毁它。
最后,最彻底的共享家园的运行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一个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而不受资本控制的实践。但是,如果这种实践只出现在山沟沟里,而不是出现在千千万劳动者身上,那么政府对它的干预就是必然的并且易如反掌的。在这个劳动者实质上没有结社权的国度,仅仅是一个村庄的这种实践都会被视为极度的不稳定因素。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说共享家园就一无是处。虽然是以某种商业化运营的方式,但是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广大劳动人民内心中的愿望。就像有的视频讽刺的那样,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处处不共享、处处要花钱的社会,它是一个充满着压迫与剥削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王耀城选择浪漫化地想象出一个六十年代的大集体:人民已经吃够了原子化的苦了。
因此,共产主义者们要做的绝不是幻想一个所谓的“共享家园”,或者拿它玩梗。我们想要共享的,绝不仅仅是几千亩名义上由个人承包的土地;我们想要共享的,是整个社会几千年来发展至今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我们要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给劳动者自行管理,我们要把所有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由劳动者行使。这才是最彻底的共享;而这个共享,不经由革命推翻这个不共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