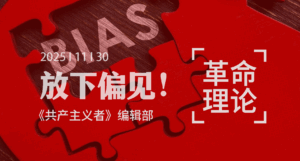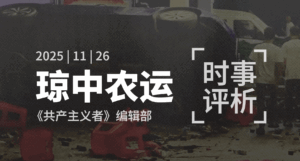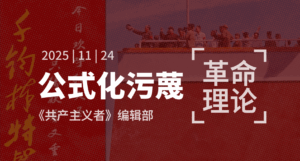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上一篇:元朝:邦统制支持下的全球化新时代
尽管元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但是其却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迅速衰败。随着商业的大规模发展,元代的国家机器愈发力不从心,苛捐杂税、官营产品供应不足或质量极差的情况也大量出现。元代前期所建立的强大财政与物流体系,依赖于中央政府对城镇经济的高度整合以及对欧亚贸易网络的制度性嵌入。然而,自14世纪中期起,这一体系逐渐暴露出其高度依赖性与极度脆弱性的两面性矛盾,最终在财政制度失衡、漕运系统瘫痪与基层治理失效的多重冲击下走向系统性危机。
首先,元代财政体系的早期成功在于其以田赋、商税和榷场垄断收入为三大支柱的“复合型财政结构”,其中商品经济所贡献的商税收入占比极高。如上文所述,市舶司岁入商税常达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两成以上。元政府为满足对海内外市场的统筹调控,设立榷酤、榷盐等专卖制度,并对盐铁茶等关键物资实施官营。但问题在于,这种官营体制在中后期逐渐陷入效率低下与腐败丛生的泥沼。正如《元史》中屡次记载,许多州县盐铁官买官鬻爵、贪墨为患,导致地方产品供不应求、质量低劣,而官营体制无法激发民间生产活力。
其次,元朝中期财政收入来源日益单一化,严重依赖漕运体制输送南方粮赋以维持北方政治中心(大都)的运转。黄河在1344年改道之后,导致大运河河段长期淤塞,漕运中断达数年之久。漕粮运输受阻直接引发京师粮荒,国家为应急而大规模调度地方物资,使得地方经济负担激增,进一步刺激民变,城市供应链濒于中断。同时,元政府治河不力,连年灾荒导致饥民遍野,农村经济凋敝,社会矛盾激化。元朝统治下的多族群统治体系此时也趋于碎片化:蒙元贵族和各地世袭达鲁花赤(地方行政长官)割据一方,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极度衰减。由此导致帝国后期皇室软弱,朝廷内部权臣争斗频繁,军队纪律废弛,对各地叛乱和盗匪束手无策。同时,元朝的赋役制度逐渐演化为“苛捐杂税”的代名词。初期设立的赋役均衡制,随着人口流动与籍贯混乱而彻底崩溃,地方军事贵族私设名目,强征滥派。正史与笔记中不乏对“鱼鳞税”、“人头钱”等横征暴敛的记载。百姓负担沉重、人口逃亡、编户制度失控,构成元朝治理体系土崩瓦解的重要前兆。
不仅如此,元代晚期财政权与地方军政权的已然无法受中央政府和文官节制,进一步导致元廷权威解体。自仁宗登基,蒙古皇室逐渐沉溺宫廷内斗,政令不出中书省;文献中屡见地方擅调赋税、收取“军需税”以供己用,甚至武力对抗朝廷派员,形成事实上的地区财政独立状态。由于地方财权不统一,中央政府的货币流通性随之恶化,货币政策的失控进一步加速了国家信用的崩溃。由于白银稀缺、铜钱短缺,元代多次滥发“中统元宝”、“至正交钞”等纸币。起初纸币推动商品交换发展,但随着国家为弥补财政赤字而过度发行,导致恶性通胀。《元史》记载至正年间物价暴涨导致货币失去流通功能,交易重回以物易物阶段。社会对国家财政的信任完全丧失,形成“财乱则民乱”的典型局面。元廷对城乡经济崩溃的反应迟缓同时对海贸与私营经济的依赖也被忽视。尽管泉州、广州等港口仍有商税收入,但由于中央财政调配体系紊乱,商人利益无法保障,逐渐脱离官府体系独立运行。泉州史料甚至有“番商不得交钞,遂绝市”之说,反映海外贸易秩序崩溃。商帮组织如方国珍一派反而组织武装控制海口,与中央对抗,进一步削弱了国家权威。
从制度视角看,元代国家治理模式极度依赖自上而下的的纵向链条结构。一旦城市经济失能,中央财政失控,边疆统治就如沙堤崩裂般不可逆转——而这种过度依赖商税与物流中枢的治理模式在缺乏足够地方自愈、自治、自产能力的前提下注定难以应对多重危机的总爆发。元代中期之后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其体制结构性失衡的深层反映。财政官营化失效、漕运体系中断、纸币滥发、市场秩序丧失,到央地矛盾的总爆发和中央权威瓦解等因素互为因果,构成了帝国走向系统性瓦解的连锁反应。元朝所曾引以为傲的商业全球化和城市网络繁荣一体最终反而成为帝国无法灵活应对危机的束缚所在。
于是,在中央失序的背景下,民间反抗此起彼伏。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起义迅速席卷各地,如上文提到的,其成分并非单纯农民:一些起义领袖如张士诚原是漕运船工出身,方国珍则为沿海私盐商人。他们利用城乡物资流通崩溃的时机起事,控制水路和海岸地区的商贸重镇,说明这场大叛乱包含了除破产农民以外城市失业者、商贩、手工业者等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而非传统史观中“农民战争”。红巾军的兴起实质是城乡经济供需关系彻底崩溃后的社会反弹,也是对元末官僚腐败和财政崩溃的全面反抗。元政府虽一度镇压起义,但大一统帝国一旦面临全国控制力总崩溃的局面则必然导致粮饷物资无法筹备、中央军事实力大不如前,最终不得不倚仗各地军阀平乱——然此举更加剧了权力下放:蒙古宗王和汉人乡绅武装割剧各地,元朝实际政令鞭长莫及,而割据和军阀混战局面进一步导致元廷失去重建起赖以生存的城市化体系的可能。至1360年代,各地以汉人、色目豪强为首的割据政权林立,公然与元廷分庭抗礼。最终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军北伐,在1368年攻克大都,元朝残余势力北上蒙古草原。
元帝国的覆亡,根源在于其基于财政、漕运、城市复合网络国家命脉在其所处的年代缺乏足够的行政管理和弹性自愈能力。随着黄河漕运危机与元代过度注重城市、在农村进行的类似“包税制”的复杂税收制度失常,其国家财政迅速破产、物流体系瘫痪,进而导致地方军阀坐大之时,朝廷也行将就木。红巾军起义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元末的覆亡体现了中华帝国最为先进的一次政治尝试所产生的国家实体内部经济生态与统治结构的全面崩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及元代统治时期积极参与的欧亚贸易网络所带来的繁荣与“全球化红利”并未有效转化为稳固的国家财政基础,反而在自然灾害和内乱中灰飞烟灭。
经历元末战乱之后,新兴的明朝统治者朱元璋汲取了元朝崩溃的惨痛教训。显然,他认为元代的统治过于依赖商业和外来因素,导致社会失序。因此,明朝初年采取了一系列“重本抑末”、“厉行封闭”、“重农抑商”的制度措施,从根本上扭转元朝的治理模式——著名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中那一句“自古以来只见过农民造反,从来没见过商人造反”的格言可以很好地概括朱氏王朝的统治逻辑。首先在人口管理上,朱元璋严格束缚人口的自由流动。他于洪武年间重建户籍制度,将全国编户齐民固定在土地上,实行里甲制和“鱼鳞图册”(类似房产和地产的集中统计文件),禁止农民离开籍贯。户籍被细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等数十种世袭身份,各户不得擅自改业迁徙。例如,军户世代供军役,匠户世代为官府手工业服务,盐灶户世代煮盐,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在行业和地域间的流动。这与元代较为开放的社会流动形成强烈反差:元朝时期大量流民、商人南北往来,经商逐利,而明初则力图将社会重新固化在农本秩序之内。朱元璋认为,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商贾的恣意流动会破坏农业生产和地方治安,因此采取高压政策遏制之。他颁布严厉法律,规定平民私自远行需持官府路引,违者治罪。有史料记载洪武年间一位书生只因遗失路引,几近被处死——幸而朱元璋临刑前特赦才免命。这种严酷的管控展现出明初统治者对流动人口的高度戒备。
在经济政策上,明初政权对元代“重商开洋”的逻辑实行了全方位的抵制和扭转。朱元璋大力提倡农桑本业,贬抑商旅之事,强调工商皆末业,不应居于主导地位。洪武期间,明廷解散元代在各大城市中形成的商人行会组织,取缔由私人主导的商业中介网络:元代后期城市中活跃的牙人、掮客在明初被视为非法行为,予以禁止。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在城市设立官方的“牙帖”制度,由持照官商垄断中介职能并限制自由市场的功能。这种做法削弱了商人自治组织的力量,使贸易活动更多受官府节制。明太祖还大幅压缩元代遗留的税卡、市舶司等机构:据记载,他即位后不久便裁撤了全国三百多处税课司局,大幅减少商税征收点。在朱元璋看来,元末社会因商贾坐大而致乱,他要重建“小农稳态”的经济基础。因此,明初的财政体系回归以农业实物地租为核心——洪武朝停止了元代行之有效但已崩溃的纸币税收,将税收主要改征实物粮、绢等。朱元璋甚至下令禁止白银在民间大宗交易中流通,以防财富过度向商贾集中。他在洪武末年颁布法令,企图废除民间货币化趋势,重申以谷、帛为市,极力降低经济活动中金融化的货币成分——整个明代,地租和徭役多以实物缴纳,并在万历年间使赋税征收恢复“地丁合一、以粮代役”。总体而言,明初经济政策对元朝的“全球化商业模式”作出了制度性反动:以前的国际贸易、货币经济被压缩退场,取而代之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国家对工商业的严控。朱元璋试图营造一个“不依赖商旅之利”的本土经济,以巩固新生王朝的基层稳定。
明初起的帝国对外贸易政策更是发生了激烈转折。元朝时期每年海外贸易额巨大,但朱元璋对此类“牵涉外夷”的商业网络心怀戒惧。即位之后,他逐步推行“海禁”的政策。早在1368年明朝建立时,他就令停办部分对外贸易事务。1371年,更明令禁止一切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往来,宣称任何擅自出海经商者一律以私通番夷论罪,可处以死刑,家属邻里连坐流放。朝廷将合法的海外贸易严格限定为朝贡贸易体系,只有外国使节奉表来朝、进贡方可进行有限的贸易交换。与此同时,明廷陆续关闭了元代的市舶司:至1380年代,宁波、广州、泉州等三大海贸港口的市舶提举司全部被裁撤。官方甚至派兵堵塞了部分沿海港湾,拆毁多桅远洋船只,以断绝民间航海之念。这种高度保守的政策,表面上是为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实质上是明政府对跨国商业资本的有意驱逐。许多元代活跃于中国的穆斯林、高丽、日本商人被迫离境,本土商人则转入走私或停业。海禁初期,中国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部分东南沿海市镇陷入萧条。同时,大批原本从事海外贸易的沿海居民转为盗匪走私,导致明政府疲于缉捕。朱元璋取缔私人商业、仅保留朝贡贸易的意图不是不要贸易,而是不要不受他控制的贸易,他一方面力图通过海禁将海外贸易完全纳入中央控制、垄断经营的轨道,另一方面允许部分朝贡国家定期进献,以此获取稀有舶来品和部分关税收益——与元代多元活跃的海商网络相比,这种装点门面的朝贡贸易规模极度有限,完全无法对社会创造普遍财富,实际上建设了政令垄断的体制、冻结了中国原本蓬勃发展的海洋商业力量,将之束缚在国家许可的狭窄空间内。明太祖此举直接破坏了元代蓬勃发展的泛大洲物流体系,使中国与迅速兴起的世界贸易脱节、埋下了日后落后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