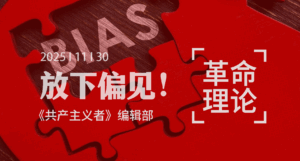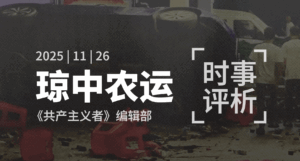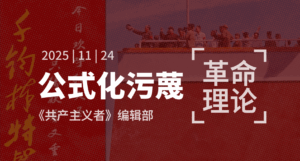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尽管宋代的国家建构较为失败,进而引发蒙古帝国南下和最早以蒙古族统治者为主的中华帝国元朝建立,但元代并未像许多错误观点所坚称的那样,导致所谓的生产力大衰退。承前启后的宋元时代应被视作一个整体,其治理下的中华帝国领土是中国从中央官僚统一掌握下的邦统制结构转变为能够资本主义逐渐兴起的半近代社会的重要时期。这一结论对于破除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政治界扭曲的“东方主义”观点,即所谓蒙古征服带来了“混乱与灾难”这一试图无中生有创造蒙古族与其他中华国家内族群的民族矛盾,且具有明显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唯心史观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反蒙、反元论实际上来自清末同期欧洲史学家的研究,认为所谓的蒙古大征服将“文明的中国汉人”改造为“不文明的东方黄种蛮夷”,通过渲染所谓蒙古入侵的破坏,在现代的帝国主义制度内将亚洲人民塑造为“二等人”形象,最终达成其诸多种族主义目的。随着中华民国时期大量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史学流派传入中国,这一偏见得以留存至今。
十三世纪的蒙古大征服令从汉城到安条克之间的全部土地处于统一的蒙古帝国管辖下,首次实现全亚洲整个一直世界与世界百分之60以上人口的大联通。征服了北部中华帝国金朝政权的蒙古帝国吸纳了其官僚治理传统与文官行政知识,在结合了蒙古先进的机动骑兵后将版图扩张到维尔纽斯-克里米亚-科尼亚一线,在版图内内内成立多个名义附庸的巨大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金帐汗国以及中华帝国领土上的中国元朝,各大汗国名义上尊中国的大元皇帝为最高领袖),而在各大汗国内部放权于原本地方实力派(例如波斯帝国的文官、罗姆苏丹国的游牧军事贵族),施行以蒙古军事实力背书、以税收为主要统治工具的半羁縻治理,并着重于维护和扩张原有基础设施,创造适合蒙古帝国刺激贸易以增长税收的物质条件,进而造就了一大批以贸易为基础、手工业和文化产业极为兴盛的多民族混居城市,大不里士、布哈拉、元大都、广州、喀山等亚洲城市要么是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在国内角色之外大规模扩充了跨国、跨大洲贸易站点的角色,要么是填充了先前城镇化网络的许多缺口,并促成了东西方技术与文化知识的互联互通,为此后亚欧各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更为充分的物质条件。
在以德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为首的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史学派影响下,许多历史学家创造出所谓蒙古大征服系统性破坏了从波斯到中国的每一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和生产力的谎言,这一谎言为日后的美帝国主义者所使用,从来起到在精神上、历史上,与意识形态上贬低、矮化亚洲民族,并借此分裂民族团结的反动理论武器。事实上,蒙古帝国在征服伊朗高原与中华帝国的过程中从未对当地经济与生产力造成高于这些区域历史上常规战争的破坏,而蒙古辖区内的经济往来几乎全部在征服后的一小段时间内迅速重建并得以在统一的大帝国体系下取得更为辉煌的综合发展。1267年蒙古帝国对于南宋前首都杭州的征服实际上是一场几乎完全和平的“接收”:尽管许多帝国主义史学家以春秋笔法的方式,认为杭州在蒙古政府前后约四十万人口的波动是因为所谓的“蒙古大屠杀”,但实际上,中华帝国首都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南宋首都光是皇家驻军、文武百官、皇室贵族以及附属于整个首都政治地位之上的统治阶级人口就逾四十万,且不包括依靠以上纯粹食利者集团为生的生产者。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南宋朝廷的崩溃,此类纯粹消费阶层集团的迅速流散与解体是十分合理的,而杭州的工商业在蒙古征服后也的确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期。然而,蒙古政权统治时的杭州,就算没有了南宋宫廷及其中央政府的驻扎,也迎来了属于自由贸易、国际交易与蒙古治下普世帝国区域商业中心的大繁荣,正如几十年后《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提到的那样。以杭州为例,一座曾经作为中华帝国南宋朝廷首都的超级政治中心,能够在被蒙古政府以后丧失政治地位的情况下,保持其约百万的人口与全东亚乃至全世界最繁荣、著名的商业港湾之一。
在经历南宋的国家机器受限于商业利益干涉而无法均衡发展的失败教训后,元朝政府力图通过减税、贸易场所规章化等政策吸引私人资本的集中发展,并通过免税或减税措施促进官营贸易场所(元代榷场,即元朝政府进行专门监管与维护的商业贸易场所)内的资本集中交易,同时推行在各商业领域使政府直接辖属的商业部门垄断商业利益的政策。在十三世纪晚期,元大都的商业贸易税收已经降至60分之1,并通过予以大规模减税的方法吸引农村个体工商户迁入城市地区发展。至元十五年(1278年)起,元政府几乎每年都下达减免商业税的诏令。对于大都、杭州、扬州等重要贸易城市,元政府更是直接颁布外商不征税以及禁止各地方政府额外征收杂税的政令,以期提振商业发展。以上主要集中在布匹、丝绸、粮食、手工艺品等产品门类,而对于盐、铁、茶、矿物等高价值作物或工商业原材料等产品,元廷则在宋代官营提举司的基础上,大规模建立总管衙门、总管府或提举司进行垄断经营。在中华帝国已经十分成熟、以各地贸易节点为中心构造的跨区域商贸网络基础上,庞大的元代官营商业得以进一步促进各地货物通过政治背书的贸易网络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以统治在继承宋代工商业组织与财政模式为基础,结合蒙古帝国横跨亚欧大陆的政治与交通资源,元廷通过重要商业部门的官营产业垄断创造了一套效率极高的交易网络,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国际化、城市结构的复合化与生产体系的高度社会化。除重要原材料以外,元代在原有织染局、造船局、铸钱局的基础上,设立织染提举司、船坞提举司等中央机构,强化对产业的集中调配能力。在冶铁方面,元代推广灌钢法的同时,依托运河体系与“站赤”(官方邮驿系统),形成了由原料产地-加工中心-贸易口岸的完整产业链。
元代以官营核心产业为支撑、私营产业的大规模繁荣的复合经济制度就是依靠整个蒙古帝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整合所建立的。在元代,市舶司制度成为国家介入和主导对外贸易活动的核心机构,不仅承担关税征收职能,更发展为集财政、外交、市场监管与港口治理于一体的综合性机构。这一制度最初继承自唐宋旧制,但在蒙古帝国统一亚欧大陆、推动贸易自由化与制度化管理的背景下,其规模与职能获得了极大扩展。元大都设有总管市舶提举司,统辖全国港口的市舶司系统;各地方政府则在泉州、广州、杭州、温州等港口设立市舶提举司,均由中央任命的文官系统主理,直属户部与尚书省管辖,此后随着管控资源贸易的统一需求,杭州与泉州的市舶司同盐运司合并,形成总辖所属周边地区对内对外贸易的都转运司。元代市舶司的核心职能之一是征收海外贸易税,如“舶脚钱”与“抽分”,其税率一般在8%至10%之间,远低于同时期西欧多数国家动辄30%以上的港口重税,极大刺激了外国商人入华贸易的积极性。泉州地方志等史料记载,泉州市舶司岁收税收稳定在一亿文以上,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而这种制度化的“低税—高流通”模式,也成为吸引全世界商人长期定居、定向输送奢侈品与战略物资的保障。如泉州,在元代已发展为世界第一大港,《元史》记载,泉州诸番舶舶,互市岁亿,其对外贸易范围东至日本,南达爪哇、占城,西接阿拉伯、波斯湾,甚至东非苏丹海岸,每年的贸易额是同期地中海第一大港口亚历山大港的一百倍以上。截止至元年间,元廷每年5分之1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对海外贸易的税收所得。
市舶司不仅征税,还负责全面管理外商注册、驻留与行为规范。各港口设有“蕃客院”安置外商,市舶司负责其住所、宗教场所(如泉州的清净寺)、翻译服务、市场置放以及法律纠纷调解等事务,确保多民族、多语言商贸群体在港口城市中得以合法、稳定地运营。市舶司同时主持货币兑换业务,在各港口城市设有兑换所,统一使用如中统钞(忽必烈执政时期的元代货币,其以国家信用支撑的金融作用与今日毫无差异)、铜钱、银锭等流通币种,为中外商贸交易提供标准化结算平台。同时,元代市舶司还参与调节商品价格,对丝绸、香料、陶瓷、金属等大宗出口商品实行价格监管,并设“检验使”负责质量把关,以维护元朝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
此外,元代市舶司不仅是财政与贸易的执行机关,也发展出高度制度化的情报与信息整合功能,成为国家了解和调控国际动态的重要支柱机构。各地市舶司通过设立在港口的“蕃客院”、外商馆舍、翻译局等多种渠道,长期收集、整理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的商贸数据、物价波动、货币兑换比率、海上航路状况与外交环境变动,并定期以呈报形式上达尚书省与中书省。这种制度化的信息回报机制确保中央政府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前线经济社会脉动,进而据此调整通商政策、港口税率、外交措辞乃至物资储备与战争准备。许多关于“蕃商得利”、“金市涨落”、“大食贡使来贾”等的官方记载,均为这一制度性运作的佐证。更关键的是,市舶司系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蒙古帝国横贯亚欧大陆的“站赤制度”形成协同网络。“站赤”作为由成吉思汗确立、其后代加以扩展的军事-交通邮驿体系,不仅负责文书传递、情报交换、人员调动,更承担部分物资运输与商业护航职能。这一网络自东起元大都、和林,中贯撒马尔罕、巴格达,西接君士坦丁堡与克里米亚,在中亚与伊朗高原地区设置了大量“站赤”,其功能性远超传统驿站,构成了一个具备信息、物资、外交、军事多重功能的亚欧“超国家性枢纽系统”。市舶司收集的港口与洋商数据可借此系统迅速传达至帝国核心决策圈,元廷对波斯、印度、阿拉伯甚至意大利城邦经济状态的精准掌握几乎全部得益于这一跨大陆治理网络的高效性与稳定性。
在这样的制度整合下,元代海港不仅仅承担出口中国产品、收纳舶来品的传统职能,而是演变为多国商品的聚散中心与亚欧经济链的“节点城市”。而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在十三世纪起屡有记载表明其商人与东方商旅合作。通过对海陆路径的系统布局,元廷实际完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海陆一体化”经济体的构建。从丝绸之路贯通的伊朗高原诸城市,到中亚辽阔草原星罗棋布的据点,再到“茶马互市”连接的汉中、成都、西宁,最后来到海上“蕃舶来朝”的泉州、明州、广州,各类枢纽城市形成了横跨欧亚、诸方联通的商品循环体系。丝绸、瓷器、茶叶、铜镜、药材、书籍、纸张等中国传统工艺品由此西运;而黄金、白银、香料、宝石、毛织品、波斯器皿则由西而东进入中华帝国。在这个系统中,不仅货物流动成为常态化、高频率的经济活动,文化、技术、人员乃至宗教观念也频繁交流,构建出一个元代所特有的信息联通网络。其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元代对于冶金、火器与瓷器等关键工业产品的输出。在元代,火药的军事应用、风箱冶铁技术、水力鼓风炉与冶铜系统化铸造工艺皆已成体系,并透过贸易传入中亚与西亚,再经由意大利海港输入欧洲。许多学者指出,若非蒙古帝国时期的大规模技术、知识传输与国际市场形成,欧洲“中世纪晚期”向“近代”过渡的时间节点很可能被大幅推迟甚至无法出现。英格兰火枪部队的发展、威尼斯玻璃工业改革、德意志矿冶革新等皆有明确技术来源可以追溯至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中亚、波斯或华北工艺。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强盛的中国……具有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条件”。
得益于迅猛发展的商业体系与遍布欧亚的国际贸易网络,元代的手工业在组织结构、工艺水平与生产逻辑上都呈现出显著的资本主义化趋势,其分化程度和组织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越前代,逐步接近资本主义工业起步阶段所具备的产业特征。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元代确立了手工业的行业性分级管理体系,官方文件中多次确认行业组织,即“行”(或行会)制度的合法地位与经济职能。《元典章》明确指出匠人并非完全隶属于官府,而是以行业自治的方式归属各自“行首”管理。行首不仅负责调配劳动力,还负责订立工价标准、裁定行业纠纷、制定质量规范,并代表整个行业与市舶司、户部等国家机关进行“统购统销”类谈判,其运作逻辑与欧洲中世纪末期的行业公会(如伦敦的金匠协会、布鲁日的纺织工会)极为相似,体现出生产过程中的高度组织化和劳动管理制度的制度化。其次,从产业结构看,元代的城市出现了大量专业化的手工业区,这些区域以固定的作坊地产为核心,结合“包工头—作坊主—自由匠人”三层结构完成分工协作。以陶瓷业为例,苏州地方志记载苏州市郊区分布有百余家陶瓷窑场,分级管理,形成自上而下的行会与管理单位,各设“匠首”统筹协调产量与运输。每座窑场雇佣自由匠人百余人,有时临时增加人力以应对出口订单,雇佣关系通过口头或书面契约确定,部分契约甚至涉及工伤补偿与订单违约金,是早期劳资契约制度的雏形。再如杭州的造纸业与制茶业,南宋遗存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以“定点采购-集中加工-批量交易”的产销模式。元代纸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中亚与波斯,在伊尔汗国等地使用频繁。造纸作坊多由资本雄厚的商号投资建造,内部设有“碾浆工”“抄纸工”“晾晒工”等工种,工序高度标准化,部分地区甚至形成“每日工资制”而非“工成计酬”,说明工人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传统依附关系,形成以劳动时间与劳动契约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体系,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劳动剥削体系支柱中计件工资与计价工资制度的模式(尽管其实际形式仍然是“初步”的)。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这些行业组织并不仅是满足简单的单次、单向国内外贸易,而是高度嵌入跨国商品链条,承担出口导向型长期生产职能,形成完整的跨国贸易产业链。广绣刺绣、明州造船、扬州纸张、景德镇瓷器均有明确的长期海外买家群体,部分行业如制糖、冶铜甚至与西亚订单进行“预付制”交易——这一切都是在上述所阐明的蒙古帝国治下统一的运输基础设施前提下才得以实现。贸易中介机构(商号、行会)与生产机构之间形成动态协作机制,如前期定金、货物保险、交付日期等安排,皆以契约形式规范。这种跨阶段、跨空间的产业协调机制,已接近近代“工场手工业-市场-金融”三位一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场所模式,同上文所述的工资制度与货币金融化发展结合分析,可以得出元代已然涌现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还没有发展为社会的主导生产关系)。最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元代在城市中出现了大量“自由手工匠人”,即不再受制于宗族关系或官府徭役体制,而是凭借技术与经验在市场中自由谋生,形成“以劳取资”的新型生产者阶层。《元典章》甚至对“市坊斗殴”、“契约欺诈”等问题作出详细裁定,说明手工业关系中纠纷普遍、契约执行活跃、民间法律意识增强,这些均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初步形态。
运力最为强大的海运行业是对于繁荣国际贸易而言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要素。元代广州与明州(宁波)的造船业进一步显示出产业规模化与标准化管理的趋势,并在元廷的指导下一步步实现官营。《元史》与《岛夷志略》均指出元代官私合营船厂普遍存在“多级工序”、“轮班制作”与“验船机构”机制。例如元廷为远洋航行设计的福船、广船、海鳅船,其建造周期往往长达数月乃至一年以上,须统一由造船行会协调调度木工、铁匠、桅杆师、帆布工、水密舱制作技工等数十类分工,各自设首领,“不得擅离本岗”。不仅如此,造船完工后须通过市舶司与水师验收机构联合检验,并报至户部备案,方可下水交易或出洋远航。这一高度制度化、分工明确的复杂造船体系在当时很难由单个船厂或船商独立完成,因此,造船业的发达不仅推动了元代造船工业的飞跃发展,更是直接促进造船系统的全面官营、官官。元廷以发达的造船业为基础开创了政府主导下的“官本船舶制度”,即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出资建造、调配并控制船舶资源,并分配与水师、商人等不同执行集团以执行外交、征税、巡防及贸易任务的制度化航运体系。官本船不仅承担对外贸易的骨干功能,也是元代对海疆与海外朝贡体系进行统筹治理的物质基础。
据史料记载记载,泉州、广州、明州三大海港均设有官船营,专门负责建造与维修官本海船,并配备常驻水师、掌舵技师与贸易书吏等多部门合作团队。朝廷通过这些官本船舶控制对外通商路线、征收港口税赋、管理海外朝贡事务,并在必要时派遣武装商船护航队随行,以保障远洋航行安全。元政府同时在东南沿海各主要港口设“海务提举司”“军船监”,直接负责官船的调配、海图规划、船员征募及沿线物资补给,从而构建起一个中央垂直管理、横向港口协作、海上与陆上资源互通的综合海权网络。在这一制度体系下,沿海地区的造船作坊不再仅是地方经济活动的产物,而是国家战略资源体系的关键节点。这些作坊所建船舶不仅服务于市场贸易,更服务于国家财政、军事与外交目标,是“政-产-贸”三位一体格局中的基础环节。比如,福船作为远洋航线主力船型,其装载力高、结构坚固、船舱多达十余间,可搭载数百吨货物与百余名人员,是执行南洋与印度洋航线的首选类型。元代曾屡次派遣官本福船使团前往东南亚与西亚各地,进行商品贸易并在沿线港口设立元廷派驻官员管理外商与税收事务。
此外,官本船舶还成为帝国军事动员体系中的一部分。在元廷镇压地方叛乱、维持南海秩序或支援海防时,往往直接征用或调度市舶司所辖官本船只。《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廷下令调遣广州、泉州两地官本船数百艘,随水师南征占城(越南地区),显示出此类船舶在国家战争动员中的关键作用。如是,元代在官营与私营产业双轨驱动下,通过行会制度、专业作坊区、契约雇佣机制和跨国订单体系,已然构建起一套兼具生产组织效率、劳资合作规则与国际市场协作的早期工业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远超以农业为基础的前代传统经济结构,更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未遂”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实践经验。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元代手工业形态的成熟发展,是东亚区域进入全球早期资本循环体系的最关键一步。中国社会在宋元之间已经部分具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性雏形——其经济组织方式从以家庭、宗族为主的再生产体系,转变为以市场为中介、以合约劳动与货币流通为支点的商品生产体系;财政体系从田赋—贡品制向工商业课税与贸易关税体系过渡;社会分工从农业—军政二元结构转化为多中心、多行业、多阶层的产业社会结构。然而,这一欣欣向荣的体系即将遭遇其前所未见的挫折,且几乎从未再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