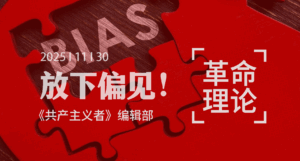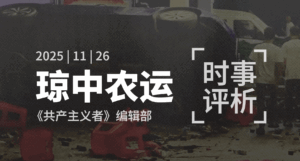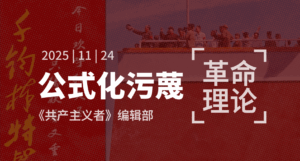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中国的电影行业似乎并不像一个面临困难的行业,它总能够给我们玩一些花样。年初的《哪吒》,就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战争;于7月25日上映的《南京照相馆》又给我们搞出了一场新的大战。
就电影所描述历史铁证,共产主义者绝对不会和自由主义者,所谓“殖人”一样为了反对中国政府而颠倒黑白。我们很清楚帝国主义对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电影的叙事方法和整体逻辑并不是单纯的记录历史,它的受众也不是平日会喜爱纪录片的人。通过对事实以特定的方法呈现,《南京照相馆》有自己的私货夹带在其中。而且,这份私货被动员起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利益,它不是“中立”的,共产主义者有必要指出这点。
对“国家”概念的模糊和“正义”对抗“邪恶”的童话叙事
战争是残酷的,只有在和平时代过久了又恰好脑子不灵光的人才会否认这个结论。几十载建筑起的辉煌大厦,几秒内就可以被炮火夷平;战争往往不仅摧毁外在的建筑,也摧毁人内在的道德观念。于是,那些在战争中被当作正常的行为,被身处和平的我们称为失序、恐怖、残忍、血腥、毫无人性与禽兽不如。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日本大兵攻占了南京后,中国人立刻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到处都是杀戮与被杀,到处都是奸淫与抢劫。人头滚滚,尸山血海——当然,影片不能只描述那些反人性的场景,否则这只不过是一场猎奇秀。一切都在于杀戮发生的原因,那个贯穿整个影片的线索:南京的沦陷,南京的社会秩序被颠覆了。
然而,这个社会秩序是什么呢?影片没有直接给出来。但是,它做够了暗示的功夫:中国从南到北的大好河山,与南京的诸多景点,以及照相馆顾客在南京沦陷前的相片。这与日军进城后的南京形成了鲜明对比:之前阖家团聚拍全家福,变成了在江边被机枪扫射无一幸免。
后来的日本摄影师,受命从象征中华民族的建筑物那里各拿走一块砖(比如北方的长城和南京的城墙),以建成所谓的“八弘一宇塔”。电影中,象征日本的旭日旗、“建设东亚新秩序”标语出现时,伴随的就是象征中国的事物的崩塌和被掠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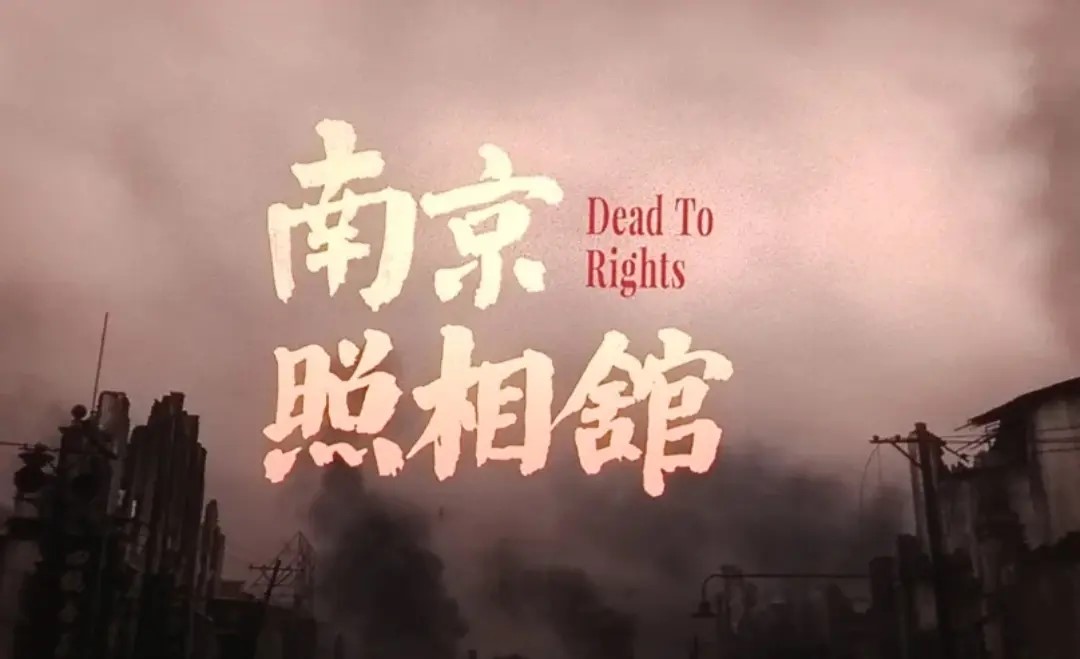
电影从此出发塑造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日本一方进行侵略、掠夺、屠杀,试图扩大自己的国家,而这必须以中国相应的缩小乃至灭亡为基础。中国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影片里,中国作为实际存在的人与物的集合,算是溃退了,中国军队在开头的溃不成军和互相残杀说明了这点;人们各顾各逃命,留下者自己学起了日语。但“中国”作为一个观念却在人们心中完美无缺,从阿昌的那句“寸土不让”便可看出来。这被视为爱国的表现。
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影片力求塑造出一个模糊、高尚而不容侵犯的“国家”概念。它屡用象征物来表达这个自己不可言状的“国”,把抗日战争解释为两个“意志”层面的国家之间的对抗。我们很难深究:爱的这个国是什么?
比如说,记录了日军罪行的照片被林毓秀带出了南京,并成为激发外国人反日情绪与东京审判定罪的重要依据。在这里,照片是记录与见证的载体,是宣传的重要工具,也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方面刻意销毁带有罪证的照片,拍摄“中日亲善”的照片。照相馆方面得知自己为日军洗的照片的性质后,便陷入了自我怀疑:为他们洗照片,就相当于当汉奸。好在电影给了他们“赎罪”的方法:把有日军罪证照片带出去。电影通过设置死局与破局的矛盾,将电影的重心放在了照片上。在这里,国家仍是一种象征体系,是影片中人物确证自己身份的方式。而从照片送出去直接跳转到其它国家的反日,也是在呼唤着如此一种预设:是国家的观念统摄着国家的物质,只要这种国家的观念还在,国家就不会灭亡。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预设。翻译王广海就说,日本这么强,中国人又是一盘散沙,日本怎么可能会输呢?严格来说,他并不真的关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观念打败哪个国家的观念,他只关心在他身边的国家的物质,这样,他才能够活下去。王广海的情人,林毓秀则不这么想。她说,日本人不把我们当人,“我们”怎么办?这就是影片演绎其逻辑的另一层需求:光是强调两个观念上的国家的对立还是不够的,因为不同国家的观念此时还只是平等地对立,我们支持其中一方就只能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能分辨出,在其中谁是正义的?
因此需要暴行,需要赤裸的、不参杂任何杂念的恶意,需要无人能辩解、同情的罪恶。南京大屠杀恰好就是绝佳的素材。日军的暴行被描绘出来了,没有日本人反对,但是所有中国人都明确地反对,其它国家的人们也明确地反对。于是,国家观念的对立被更高的道德评判。日本人完全违反了道德的原则,因此日本是坏的、邪恶的;中国人与其它国家的人们遵守了这一原则,因此他们是好的、正义的。正义打败了邪恶,这是大多数天真的童话故事的套路。
为了完成这一逻辑,电影还涉及了一条小线索。伊藤秀夫为了洗照片,把阿昌叫做“朋友”。但是,在伊藤秀夫伪善的面貌全部狰狞地露出来后,阿昌说:我们永远不是朋友。伊藤秀夫形象的反转,说明电影把他的逻辑贯彻下去了。它不仅要在国家之间分出善恶,还要在人之间分出善恶;人的善恶则依国家的善恶而定。至此,电影的逻辑完成了。它直接地具有了与现实结合的意义,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套评判现实的准则,而这些准则,最后都落到了观念上国家的正义与否。
荧幕之内是战争,荧幕之外也是战争
影片内,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于是,影片外,中国人就不把日本人当人。在一些人眼里,一切有关这部电影的争论,都可以归结为中国人与日本外务省的斗争。抛却人性,是日本军官上给新兵的重要的一课,于是,一些中国人便有样学样,抛却了思考,把所有的情绪都建筑在国家的观念上了。他们不在乎自己逐渐与电影里的日本人长得越来越像,他们只晓得盘算,如何把日本在中国做过的事,在日本再复制一遍。反对的言论,于是都成为日本外务省的安排,他们便进一步不把持异见的同胞当人了。
称颂这部电影的人中有不少还会批评《南京!南京!》,仅仅是因为其中塑造了一个有人性的日本军人角川,因为不把日本人当作禽兽,他们的叙事就进行不下去。他们既希望日本作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人一样背负责任,却又不接受把日军塑造得真的像人。因为只有这样,“夷平日本”的言论才能在理论上成立。
这种“爱国情怀”最终是廉价的,毕竟“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一个庇护所”。电影里,日本人好歹还会假惺惺地说一句:我们是愿意和中国人做朋友的。电影外,因为这一层“历史的仇恨”,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则这一套包装也不需要了。中国品质上最恶劣、思想上最肤浅并受人操控的一批人,在这个电影的鼓动下,得以把自己服务于最反动的立场、渴望犯下最恐怖的罪行包装的如此冠冕堂皇。他们和自己所仇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除了皮不一样,里头是一致的。
也许某些人需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叙事,而是发表廉价爱国言论的机会呢?须知,这种爱国情怀的结局反而是让爱国失去根基。电影之外我们也不乏滑稽戏看:网传小孩看过电影后,回家将日本卡片剪掉。在荒诞的剧目中,我们又一次看到那残缺的逻辑的显现。仇恨可以被消费了,爱国也是。他们拙劣而滑稽地表演着仇恨的样子,所求不过那一点流量,结果只会让他的所谓情怀更廉价。
在这里仍然有尚未解决的问题:国家的观念为什么能够统摄国家的物质?国家的观念是怎么来的?“人性”的观念又是怎么来的?“爱国人士”们很少这样的询问,因为国家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是现成的,无需反思的。可是,如果要既承认爱国又承认人性,就需要认为人性中就包含着爱国,于是爱国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先验情感;而且爱国是一种对特殊群体的要求,人性则是对所有人类的普遍的要求。究竟是爱国所涉及的主权更高,还是人性所涉及的人权更高呢?结果,在实践中,爱国还是成为了一种道德原则,并且能够以此开除别人的人籍;人性则足以为他人的没有人性而被忽略。
“反思”、“铭记”历史?利用、剥削历史!
国家之间的对立为何而存在?民族国家的存在本身,就为自己设立了限制。它把自己限制在一定的地域之内与其它国家相对立,这本身就为冲突埋下了可能性。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从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造成的区隔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国内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依靠民族主义来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在电影中,南京在战争前是中国人的城市,在战争后也是中国人的城市。它在试图强调一种社会构建的连续性,一种以民族为标准的连续性,于是,只要是中国的城市,便是中国人民的城市,民族内部取得了完全的同一性。
但是,这种同一性只有靠不断排斥异质性才能生存。兄弟阋墙的事发生的可不少。在强调私有权的市民社会,恐怕很少有人因为你是同胞就免费给你包吃包住,资本家也不会因为你是同胞就减轻剥削。如果中共真的找日本“报仇”去了,也只会让资本家们赚的盆满钵满,无产阶级收获的则只有战争带来的恐怖。
中国现在流行的这批电影(比如同期上映的《东极岛》)和反思历史、铭记国耻搭不上一点关系,因为理智的思考在这个市场里没有消费,更无法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他们十分热衷于自己扒开自己的伤疤,利用、剥削中国人民历史上所受的苦难,以歌颂这么一个计划:
强军!备战!大炮是用来丈量国土面积的。外国人曾经不拿我们当人,那今天,我们也不把他们当人!
这个计划的前提是:
你无条件爱你的这个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的“民族”。你不能对我国的政权提出质疑,不然你就是叛徒。
这个电影的误导性因此再清楚不过了。统治阶级把历史的不幸用自己的叙事方法呈现出来,以转移矛盾并为自己政权现在的所作所为提供“正当性”。这种题材下,不服务于这个目的的电影,一方面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还甚至会被打压(因为它破坏了这个民族主义的叙事),一方面会因为缺乏被欣赏的市场而中道崩粗。
因此,我们要做的,应当是先质疑民族国家这一观念本身:凭什么不同的民族之间要以这样的形式的对立?凭什么要让资本家与官僚的政府代表民族?当工人阶级打破民族国家的枷锁时,他们就会发现:该仇恨的另有他人。
中国工人阶级需要从这种宣传中醒来,认清自己的敌人不是未曾谋面的他国人民,而是把锁链拴在自己脖子上,拿自己当狗、使唤着去冲“敌人”叫的统治阶级。那时候,我们才能有除了高喊“打倒小日本外”,打倒我们工作场所、我们社会、我们国家里的这些剥削者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