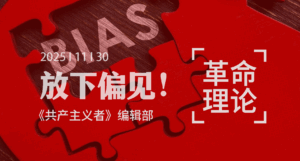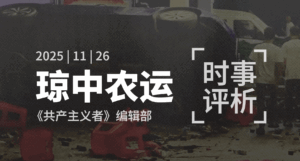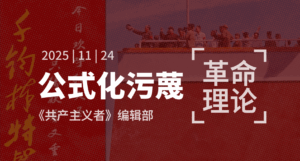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河南嵩山少林寺,这座被无数宣传材料渲染为“东方智慧”象征、中华文化瑰宝的千年古刹,在2025年7月27日的那个傍晚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官方一纸通报宣告,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罪名包括挪用和侵占寺院项目资金与资产,以及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一个被包装为“新时代宗教领袖”、被海内外媒体称为“少林CEO”的人物轰然倒塌,成为舆论的焦点。
许多人愿意把这视为个别僧人的道德沦丧,甚至认为这仅仅是一场少见的丑闻,然而,这场风波绝非偶然,而是中国社会如火药桶般即将爆炸的阶级矛盾的显现。释永信的倒塌绝非孤立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危机和官僚体系统治压力结合、以对宗教的长期异化为媒介所导致的必然产物。正是这种结合,将一座古老寺院彻底改造成牟利机器,将信众的精神寄托变成可以定价出售的消费品,并将宗教领导人推上企业家的宝座。也正是这样的结合,导致释永信作为这一体系代表的垮台。
二十多年来,少林寺逐步脱离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刻板印象中的清净精神,成为以市场逻辑为驱动的庞大商业帝国。门票收入节节攀升,一年数百万游客,光旅游门票就带来以亿元计的现金流;围绕少林品牌的授权遍布全国乃至全球,包括功夫表演团、保健产品、旅游地产、影视版权、武术学校,甚至海外分院。少林寺已不是求道者的净土,而是资本支持下消费主义的轮回之所,是地方财政的摇钱树,是宗教品牌化、商业化最成功也最赤裸的案例。释永信正是这一切的操盘手,他拥有现代企业家的所有特征:熟练的品牌运营、娴熟的谈判技巧,却丧失了人们脑海中僧侣本该坚守的戒律与出离精神。当宗教与资本结合,逻辑就彻底改变了。信仰不再是心灵慰藉,而是可以定价的商品;参拜、开光、祈福都可以明码标价,修行课程变成收费培训,所谓的佛教智慧成为广告噱头。寺院不再关心信众的精神成长,而是统计游客数量、评估收益报表。少林寺不再是信众追求宁静与觉悟的道场,而成为了功夫表演的景区,成为了商业品牌的营销基地。这是中国近二十年来宗教市场化、旅游产业化和地方财政依赖景区经济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视寺院为财政收入来源,释永信拉来投资所依靠的资本家视其为品牌资源,少林寺内的宗教精英视其为个人利益的攀升工具——释永信垮台后,一切照旧,新的住持很快面带微笑登上舞台。少林寺的一切繁荣建立在对天真的劳动人民之朴实信仰的剥削之上,信众为香火与法会掏出真金白银,却得到一场资本化表演和商品化的虚假安慰。
释永信不过是这部机器的明星齿轮,他的“成功”完全来自地方政府的勾连、使少林寺享有特权地位,宗教品牌化带来的巨额财富又让资本蜂拥而至。在这样的体系中,个人品德的堕落绝非偶然,而是被资本主义市场所看重的特质——对权力的顺从,对资本的敬仰,对信仰精神的抛弃。
人们或许会问:既然释永信的生活腐化和财务问题早在2015年就有人实名举报,为什么当年没有查处?那时自称“释正义”的僧人公开指控他生活淫逸、财务黑幕、包养情妇并有私生女,但调查不了了之。答案很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未允许触碰这一利益链条,宗教资本化仍是地方财政和宣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连中央政府都还能容忍这样的行为越做越大。十年后的今天,局势变化了,地方财政压力陡增,中央反腐持续推进,社会舆论对宗教商业化的质疑越来越多,这条曾经稳固的利益链条出现了裂缝。显然,释永信的倒台并不是正义觉醒的象征,而是中国政府内权力斗争扩大化的副产品,是体系内部自我调整的结果。今天倒下的是释永信,明天可能是另一个“宗教企业家”、人民企业家。只要市场经济所主导的、对宗教、信仰和一切上层建筑的异化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释永信。
我们要求的不是通过体系内部的修正来改善宗教,而是让群众在掌握物质生产资料之外也掌握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分配权。宗教作为历史特定阶段的现象,已经落后于当前生产力巨大发展的信息社会,势必要在未来消亡。宗教如今还能生存繁荣,完全是因为它被进入晚期的资本主义看作延长寿命的盟友。无产阶级应当坚持无神论观点,则作为战线的一部分,首先就会要求宗教不再服务于资本的无限增殖,折去资本主义的一条臂膀,进而促进宗教消亡。只有当无产阶级群众掌握社会的全部资源——这当然包括宗教和精神资源,他们才不再成为官僚与资本家的附庸。
释永信事件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宗教资本化、资本主义和官僚主导下的社会精神异化的全部丑陋。不仅是宗教,革命文化遗产也面临这种处境。我们必须看清楚,只有推翻这种将信仰异化为商品的制度逻辑,广大群众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解放。否则,即便释永信倒下,未来还会有无数个“释永信”从这片土壤中再度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