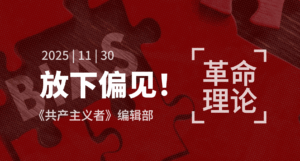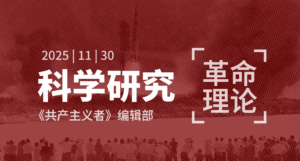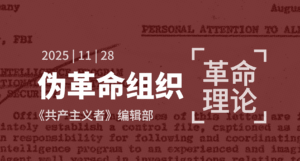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利益上自然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着某种“共同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关系的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与被占有、剥削与反剥削。但马克思也并没有忽略阶级社会内部为了维持整体秩序、促进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合作。只不过,这种“合作”和“共同利益”,从根本上说,是被统治阶级在被迫、被引导、被诱使的前提下的配合。
在面对可能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巨大灾害时,比如说大规模自然灾害、全球瘟疫、灭绝性技术风险等,阶级内部的矛盾在表面上往往会暂时让位于一种更广泛的、以“人类”为名义的团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必须共同面对危机。那种本来用于促进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在极端情况下就成了组织全社会抵抗风险的工具。此时,即便在形式上双方拥有了某种“共同人类利益”,比如生命安全、生存环境等,但这样的“共同利益”并不足以消除阶级矛盾的根本性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统治阶级也必须满足被统治阶级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否则整个社会将无法继续运转,连统治也无法为继。同样的,在危机下,如果统治阶级彻底无视普通民众的利益,不仅其统治合法性会快速丧失,社会稳定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即便在危机时刻各阶级能够“团结”,也是因为现实压力和历史教训逼迫出的一种临时联盟,而非阶级冲突的根本解决。等到危机过去,阶级关系必然会恢复常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会和以前一样不断发生。
因此,统治阶级即便是不情愿,也要在某些时候对被统治阶级作出让步,或者至少表现出某种“回应”和“关心”。但这种回应通常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带有策略性。葛兰西曾提出一种所谓的“被动革命”,正是指统治阶级主动或被动地对下层诉求有限接纳,以防止更激烈的变革。
不仅如此,这种临时的“团结”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在此时的消解。事实上,在危机之下,阶级矛盾常常表现得更加激烈和复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共同灾害的回应需要,但在具体的利益分配、资源投入、“灾后重建”等问题上,阶级本性往往很快浮现。在灾难面前,本应以全社会利益优先的原则,经常被统治阶级垄断资源、优先保护自身利益的操作所替代。比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遇到大规模灾害,最先获得资源、保护和信息的一定是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被统治者则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疏忽、牺牲的命运。甚至在“人类利益”的名义下,统治阶级还会利用危机机会掠夺公共财产、攫取额外利益。比如“投机者”趁乱大发灾难财、官僚阶层敷衍塞责、贪污腐败等现象,在这种危机时刻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在表面应对危机的同时,实际上也依然在追求本阶级利益最大化,靠妥协和让步换取稳定,却不会真正放弃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
更重要的是,危机不仅在现实层面激发阶级斗争,还会在舆论、文化、道德等领域推进被统治阶级的激进化。每一次灾难,对统治阶级的公信力、统治方式、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检验都更为激烈,也会加速底层社会的反思和自觉,推动新思想的传播。因此,尽管在表面上危机带来所谓“人类共同利益”,这种共性也很快就会变成各阶级利益再分配的战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必然以更隐蔽甚至更暴力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东汉末年,瘟疫与饥荒并发,朝廷以“同心救灾”诏书动员各地乡绅出粮、佃户出力,但灾后乡绅们立刻趁机兼并土地,将赈灾债务转成高利贷,荆州饥民被迫“以身为质”,因此才会有黄巾军的创立,其“苍天已死”之口号也流传甚广,灾后人相食的记录也成为了农民揭竿而起的“动员令”。
在黑死病席卷14世纪西欧时,封建领主与农奴突然面对同一种无差别攻击人类的鼠疫杆菌,这场生物层面的共同威胁迫使双方暂时进入“防疫共同体”:领主同意减少地租以便农奴留在庄园耕作,农奴也接受领主调配去焚烧尸体、堵塞鼠洞,表面看来阶级关系被灾难软化,然而瘟疫一过,领主立即利用人口锐减的“买方市场”优势收回土地、提高租金,甚至把幸存农奴已耕熟的份地圈作牧场,农奴则以逃亡、怠工、焚烧庄园账册的方式回击,阶级矛盾在灾后以更赤裸的掠夺与反抗爆发出来。
19世纪末的印度饥荒被英国殖民当局宣称为“帝国臣民的共同灾难”,伦敦调运粮食、修筑铁路赈灾,然而在运输途中大量小麦被转口到欧洲市场换取英镑,印度饥民只能以掺土的面粉糊度日,灾后粮价飞涨,殖民政府却以“财政纪律”为由加征土地税,饥荒幸存者被迫卖身为债役劳工,民族主义者提拉克、甘地便把“救灾”话语改写为“殖民掠夺”话语,推动反英群众运动走向高潮。
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国民政府与列强共同呼吁“救灾第一”,上海银行团以“救济”名义向灾民放贷,地主却以工代赈逼农民修堤换口粮;在洪水稍退时,国民政府又立刻加征“水利捐”偿债,地主们也收回了被淹田地并将租额提高三成,这直接导致了鄂豫皖边区农民在“均粮”口号下涌入红军,水灾刚过农民们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六安县苏维埃。
2020年欧洲新冠疫情初期,欧盟委员会高呼“全欧健康共同体”,德国、荷兰政府开放重症呼吸机给意大利,然而疫后复苏基金以紧缩为条件,南欧诸国削减公共医疗与工资,布鲁塞尔街头的“为生计而游行”与巴黎郊区的“反疫苗通行证暴动”在口罩尚未摘下时便把各阶级“共患难”的叙事撕碎,民调显示最强烈反对紧缩的正是曾被视为“欧洲团结”象征的医护和物流工人。
综上所述,阶级社会中确实存在某些特殊时刻,各阶级必须维护“人类社会的延续”这一共同利益,统治阶级确实需要调用被统治阶级的劳动与服从才能保存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于是出现“全人类利益”的修辞与暂时协作;然而灾后恢复总是以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更集中占有、对被统治阶级剩余劳动的更深度榨取为结局,被统治阶级在“共同抗灾”中获得的微薄让步旋即被收回,甚至成为新一轮剥夺的起点,阶级矛盾因此不是被灾难消弭,而是在“同舟共济”的短暂幻象之后以更加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危机只不过是把矛盾推向新的斗争阶段,或者促使其以更加复杂、激烈的方式爆发。阶级统治的可持续,从来不是因为消弭了矛盾,而恰恰是通过不断制造、调和、重新分配这些矛盾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