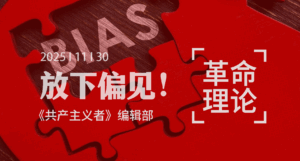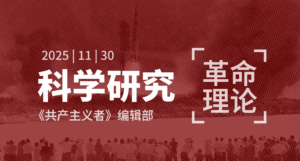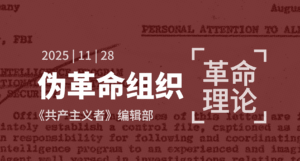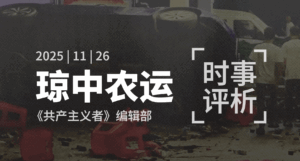鸿运齐天
2020年,当丁真去他舅舅家吃饭时,碰上了改变了他一生的摄影师胡波,恰巧的入境使他迅速成为了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相关影片展示着他纯真无比的笑容,使有关这个笑容的讨论在热门的短视频平台抖音迅速变得火热朝天。拜互联网的传播力所赐,丁真迅速走红,其原因非常简单粗暴:丁真的笑容所展现的草原生活的淳朴,在日益枯燥乏味又功利导向的现代社会,触动了人们内心的对于回归本真质朴、自然和美的向往。随着关于“丁真”的讨论越来越热火朝天,甚至出现了国际化发展的趋势:韩国的《中央日报》也在随后报道了丁真的笑容,丁真本身的“价值“开始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就像狗闻到屎一样前赴后继地去到四川理塘当地进行追踪报道,顺带着,整个理塘也因为丁真一人的走红开始备受关注。
四川文旅反应非常快,同年11月25号就已经和时差鸟联合出品了由丁真参与拍摄的礼堂旅游宣传片《丁真的世界》,获取广泛关注度,理塘摇身一变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互联网流量给理塘带来了泼天的富贵,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和自媒体,人人都想在这波热潮当中分一杯羹。同年11月29日,中国官方下场表明态度,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连发三条英文推文向海外网友宣传丁真。2021年2月,丁真首次在卫视春晚登台亮相,并倾情演唱了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从此,丁真身价水涨船高,先后参加了联合国演讲,担任了理塘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国企员工,并成为了在中国互联网上一个代表着流量的标杆人物。
但是,随着丁真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越推越高,相关的批评开始涌现。网民对丁真这种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藏族牧民,仅仅是因为一张纯真的脸庞就能够获取大多数人无法获取的社会资源感到非常不痛快,许多寒窗苦读的人士历经千辛万苦才能获取的国企职位,他只需要一个笑容就可以获取,这显然在嘲笑和戏弄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奋斗和努力,这引发了公众对于丁真这种“走红”的道德合法性的严重质疑。不过,这种质疑很快被媒体机器筛选灭杀,当批评开始愈发尖锐地指向社会的分配制度时,不知来自何处的神秘力量迅速压制了这种声音,并且它派出了它的先锋喉舌——2020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发表署名杨鑫宇的评论文章《“做题家”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使用网民反映接受过应试教育的自嘲“小镇做题家”,批评攻击者将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投射、宣泄在丁真个人身上。批评的声音遭到媒体机器的绝对暴力镇压下,开始走向了解构主义的道路,批评群体被迫只能拿着无关痛痒的点去进行批评,例如只是对丁真在采访当中说错话、抽烟等进行艺术加工的恶搞,内容上越来越远离了它的初衷——对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和畸形的国家经济发展策略的不满。
囚徒困境
这一次也是辩证法的胜利,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小镇做题家”们对丁真的批评,到底是不是源于他们人性当中丑恶的嫉妒、嫉妒丁真那样俊俏的脸庞没有长在“做题家们”的脑袋上、嫉妒丁真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获取到他们获取不到的资源呢。
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做题家们”的抱怨到底是不是真的?诚然,无论营销团队和官方如何在丁真“山鸡变凤凰”后“揠苗助长”,都不能短时间提升丁真的知识文化水平,这种由内而外的气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装出来的,答案无论怎么样做修饰,都不能有一丝的改变——那就是丁真确实没有在学业上付出过和大家对等的努力(在这里可能会有人说这是因为丁真的资源问题,不过这是另一个领域的探讨,下文会回到这个问题来),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系统的文化教育。按理说,中共一手渲染起来的国企岗位的“登天之路”,先不说丁真有没有资格参与,而是丁真本身的能力,公共知识储备,居然任何考核测试都没有通过就获得了岗位,破天荒地违反了大家对于考核竞争的一概印象,且所持有的筹码,仅仅只是一张羡煞众人的俊俏脸庞。这就是摆在大家眼前板上钉钉的事实。那么可不可以说,一张俊俏的脸庞和纯真的笑容,是等值于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和坚持不懈的呢?就算我们不做具体的量化,二者也根本就没有可比性——答案非常清楚,“做题家们”一点也没说错,所谓的“稀缺资源”,即颜值,就这么潇洒地踩着无数人的汗水登上象牙塔尖,丁真的成功,讽刺了所有“做题家们”的辛苦付出,原来都比不上别人一个笑容。那么“做题家们”的这种抱怨就不是错误的,甚至这都不是抱怨,而是面对这种不公分配的合理质疑。
那么官媒是怎么回应这种质疑的呢?像杨鑫宇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文章中公然写道:倘若一个“做题家”的生活基本令人满意,足以回报其求学生涯中付出的努力,他根本就不会去在乎这位康巴小伙是否幸运,以及他又是靠着什么才得到了这种幸运。明里暗里都在批判着大众的质疑,认为大众的质疑本质上是对自己无力改善生活的无能狂怒,只能将这种对自己不满的情绪宣泄到成功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如此傲慢的、姿态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他作为统治阶级的喉舌,作为官方媒体的其中一个代理发言人,先是以一种极度丑陋的姿态回避了大众最初的核心质疑——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更是反过来倒打一耙,攻击大众是心理不平衡的狂热犬儒,无法接受别人的成功而只能无能狂怒。
问题出在哪里?首先,“做题家“这个称号,是多么的令人无奈。它的背后是莘莘学子们无法量化的奋斗,在每个挑灯夜读的晚上,无数人绞尽脑汁背诵,解题,为的却是一个十分迷茫而不稳定的将来,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每一位都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极有可能发生的是,即使他们已经拼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应付考试,却依然名落孙山。这真的是因为无能吗?事实绝非如此,那些只占有”自由“的无产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有责任异化自己,向资本家阶级展示自己创造利润的潜力,向统治阶级展示自己的意识形态服从度,就像把自己变成一个商品一样放到劳动力市场上任人挑选,或者是把自己改造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绝对傀儡,这样他们才能获取劳动机会,从而保障自己的生存。所谓的”做题“,只是无产者被允许拥有的机会,然而他们还是需要互相斗个你死我活,尽管在统治阶级眼里这是合法且正义的,因此那些被排行榜折磨到死的“做题家”,他们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苦心打造的产业后备军,是那些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最需要团结的劳苦大众,是真正掌握着社会运作的劳动阶级。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半路突然杀出来一个丁真,他无需参与任何的考核,无需付出与他人相当的努力,他只是在镜头前笑了笑,于是就莫名其妙地取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他迅速跳过了所有的考核步骤,获得了劳动阶级们争得头破血流都争不到的资源。问题就出现在这里——统治阶级口舌有为此作出解释吗?答案是没有的,他们至今都逃避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回答为什么它们自己一手建立的严格的晋升考核制度如今可以如此儿戏,如此不严谨而又如此不公平,他竟然还要反过来,攻击提出质疑的人是“嫉妒者”。
紧接着,统治阶级口舌下了一步极为阴险的棋,那就是利用群众的质疑去攻击群众,并分化群众本身。通过攻击群众是无能的嫉妒者,统治阶级成功将问题的焦点从丁真背后可笑的不公制度转移到丁真本身,并利用丁真来吸引部分群众的同情,从而进行群众的分化瓦解。它首先利用它的国家机器控制群众的质疑声音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并派出它的忠实信徒当所谓的“讲公道话”的“好人”,他们大力鼓吹反对对丁真的网络暴力,并从而误导部分群体对丁真的遭遇产生同情,从而让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丁真的“成就”,打消自己对背后制度不公的“质疑”并合理化自己被剥削的事实,矛盾的焦点转移后,统治阶级正好就可以利用所谓的网络暴力的理由进一步将批评压缩得所剩无几,以至于红线终于划到了劳动群众们退无可退的地方。从而,对丁真现象的质疑开始走向了它的表面——它愈加流于对丁真本身的攻击,批评开始走向解构主义,由于统治阶级的机器暴力,劳动群众无法再直击问题的本质核心,而是开始对丁真本人的特质进行恶搞解构,嘲笑丁真本人的口音、失误、行为等,随着时间的沉淀,丁真也越来越在表面上脱离了“丁真现象”,尽管我们极富创造力的劳动群众,在黑暗中依然发挥了他们最伟大的主观能动创造力,通过填词作曲来隐晦地表达对制度的不满,但是相关的批评作品缺乏系统梳理,信息非常发散,而且为了掩藏真实目的又不能不流于形式和表面,因此不免又导致了部分群众倒向对丁真的同情——至此统治阶级的目的已经达成,群众已经不甚团结,对“丁真现象”——即“灵活无比”、可操作性极高的分配制度的批评,变成了对丁真本身的批评,攻守交换了,群众的质疑变成了统治阶级手里质疑群众的武器。
无产者们进无可进,退无可退!
提线木偶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批评丁真,从来不是因为他抽烟,或者是在直播采访中说出一些惹人发笑的话,而是批评丁真的出现,反映着的是那个被统治阶级粉饰得极好的、所谓“公平“的竞争制度,它表面上大手一摊表明人人都有这个机会去争取,失败不是它的责任,但是它却可以高高在上地当这个规则的话事人,随意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操控这个制度,而并不会选择去遵守自己一手建立的制度。一方面,这和资本主义的虚伪面庞异曲同工,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统治阶级总是将所谓的“普世价值”大力宣传开来,脱离实际生产关系地去用各种道德礼教规训人们的行为,但是往往他们自己就从不遵守这些规范,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关于家庭和家庭专制主义》一文中所提到的:资产阶级十分伟大地表明它以先进的制度打破了封建专制对于家庭的规训,强调个人婚姻恋爱自由,表明自己没有权利干涉个体的婚姻,但是往往资产阶级本身的婚姻是最不自由的,因为它对婚姻所起到的物质继承和再分配的作用比无产阶级要来得更为病态而强烈。另一方面,这无疑是向我们展现了无比清晰的一点:那就是一切的带有私有制色彩的统治阶级所设计的竞争制度,无论它如何用言语做修饰,如何在形式上迫切地展现它的公平,它总是本质上作为统治阶级用来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它给予了一个“希望”予广大无产阶级群体,让无产者们为了生存忘乎团结,互相争个头破血流,这样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统治阶级便可高枕无忧,享受无产者内斗的劳动成果,因此,他们最为鼓励竞争,并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每一个无产者个体上,然后故作姿态地表明个体的失败和它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无产者自己能力不行,而且在这个被设计好的制度中胜出的无产者,会非常自然地沾染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多数会反过来攻击他们的阶级兄弟姐妹,而不是同情他们,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无产者们便会开始麻木,并丧失对制度不公的怀疑。
而且丁真一事,笔者认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中共统治阶级为什么会突然大发慈悲地帮扶一个四川山里的康巴汉子呢?这个问题的来由就是在丁真之后也不乏有相似的来自草原的一些俊俏男子也尝试复刻他的成功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只有丁真是幸运的宠儿呢?难道说是中共文旅部长看到丁真的纯真笑容后春心荡漾,脑门一拍决定就捧他?还是说中共有风水大师对照了他的时辰八字,发现这人能保中共江山永存?无论怎么想,这都是很诡异的一件事情:莫名其妙的走红,莫名其妙的捧红。
中共到底获得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它现在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不会做亏本买卖,至少不会想做。因此捧红丁真,一定有它的利益需求。我们就来看看中共在2020年到底在面对着什么。首先,中共在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已经快要到达临界点了,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了3年,中共内部软弱的官僚资产阶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样,面对帝国主义的突然发狂和歇斯底里只会选择让步和退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地位和统治,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关税加码,它只能选择大幅度压缩出口商品的货币价值,从而打破美帝国主义的贸易壁垒。但是这有一个很明显的代价——那就是成本的扣减一定是从劳动力开始的,商品要变得廉价,那就必须低附加值,因此一定要压缩劳动力成本,但是商品高度流动需要货币的高度流动(马克思所说的货币交易掩盖商品交易的假象),因此一定会带来通胀,这就导致了劳动力价值跟不上商品交换价值的增幅,甚至二者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自2018年起,经济明显开始转向下行。同时,新冠疫情的出现带来了两个对于中共来说非常棘手的问题:第一是疫情防控大幅度减缓了商品生产,甚至是导致商品流动停滞;其二是使中共在国际舆论上占据下风,在中美摩擦进入白热化的同时,中共极度需要扩张和改善国际政治影响力。
中共有几个问题需要同时解决:第一,必须抵消贸易持久战带来的冲击;第二,疫情导致实体商品流通近乎停滞,需要另辟蹊径;第三,需要在国际政治的舆论场上扳回来,而且第一步要在国内稳住舆论阵脚,因此最好的工具是民族主义。
仔细想想,丁真的出现,恰好就撞在了这个枪口上。实体商品流通的停滞,需要大量的消费去刺激它“秽土转生”,而恰好还真的有这种转生术——那就是互联网虚拟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在那几年间“直播带货“犹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冒头,同时,许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的互联网文化的精神生产,也开始被鼓励起来,因为它能最大程度地刺激到大家掏空手里的钱包去帮助商品流通,打卡成为了一种文化,许多形式主义的消费也被疯狂鼓吹。而丁真,就是其中一员,像丁真这样的互联网流量代表,就是在2020年后迅速野蛮生长,这种精神生产刺激了大众为互联网经济买单——周边,打卡,旅游,联动商品等。这也是为什么,四川文旅和中共对丁真的出现甚为紧张,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大发慈悲想要帮丁真改善生活,而是他们急需一个又一个的互联网噱头来帮助刺激商品流通和货币的流通。其次,丁真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帮助中共在国际上进行政治性宣传,新冠疫情和美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导致中共急需在国际舆论上找回场子,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而丁真就代表了中国内地独特的一方民族文化,以此来作为宣传,尝试利用丁真的民族特色来作为扩大自己国家机器的文化影响力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作为中共的头号喉舌,会如此积极地连发三条推特进行宣传,目的就是在中共意图利用这种独特的文化产物在国际上争取视线和支持。最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历史深厚而源远流长,中共有责任促进民族的融合,以及展现民族融洽的相处,这不是因为它真的很关心每个民族,只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它的统治而已,而且在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时,民族主义总是最好的团结手段,因此中共也尝试了利用丁真的少数民族的身份,来加强劳动群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从而使他们将视角重心能够放在“宏大的”历史发展和国家人文上,以及门外的美帝国主义者们,从而能够更加忍受自己被剥削的处境。
因此,丁真是不是丁真,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在合适的时间出现,被中共利用起来满足他的利益需求,所以在本质上他更像是一个提线木偶
饮鸩止渴
丁真事件里比丁真更值得玩味的,就是丁真背后的四川理塘——理塘背后的反映的中共的地方经济发展策略的“饮鸩止渴”。
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就要问中共一个问题了: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先富带动后富“在哪里?上海如今纸醉金迷,霓虹炫彩,为什么体现不出他的老大优势,帮助四川理塘发展呢?丁真没有文化是丁真的错,还是理塘的错?还是四川的错?还是中共的错?为什么四川理塘的发展可以如此落后,为什么先富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后富当中去?为什么丁真不可以一早就享受到教育的福利?为什么地方的经济结构可以畸形到必须依靠一个人的流量名气才可以撑起?
无数像理塘这样在丁真走红前籍籍无名的中西部乡县城镇,他们为改革开放贡献了他们仅有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换来的却是东部城市的贪得无厌和中共政策的偏袒,它们长期处于一种缺乏政策支持、缺乏劳动力、缺乏天然资源的处境。20世纪80年代起,为了给开放让步,刺激市场经济发展,中共实行地方财政包干,由地方政府决定经济发展策略,中央和地方只需要签订税务合同,每年地方只需要上缴固定比例的税款,其余由地方政府作自由支配。我们的自由市场真是“太伟大了”!它直接催生了地方经济壁垒以及土地财政的畸形应用——为了争取税款指标,众多东部城市直接选择了快准狠的方法,那就是让渡土地使用权,利用政策优势带来的虹吸人口效应,迅速导向房地产产业赚取暴利。而中西部城市呢?地方劳动人口流失使农业一夜暴毙,三农问题开始扼住了农村的咽喉,欠缺优势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使它们又难以发展出完善的工业化产业,地方经济政策的自主权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促使他们在地方的竞争中迅速败下阵来,缺乏资金投入到长期回收的产业上——例如旅游业、农业、畜牧业。因此在21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西部落后的地区一直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给予了这些地区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创造所谓的互联网精神生产——诸如一切抽象文化,成为亚文化圈的代表,并以这种知名度来吸引人们为此一些相关产品买单,甚至依靠这种互联网带来的红利鼓吹“圣地巡礼”,带动地方的商品流通并从而完成地方原始资本积累,从而发展属于地方的独特产业。不过,像这种依赖观众老爷的心情来吃饭的产业,这口酒一口一口喝的舒爽,但是资本的积累和逐利能否让地方财政去做更为稳固的长期实际生产投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丁真——或者说,还有不知道多少像丁真未走红前这样的可怜的孩子们,此刻还在烈日当中挑山动地,或是在凛冽寒风中搓烂了双掌的皮,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其实只是中南海里面的某张红头文件轻描淡写的一笔。一切都不是丁真错;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努力学习不是他们的错;被中共统治阶级当提线木偶来获取他们的政治利益也不是丁真的错。错的只是机械唯物主义者里那个天真到惹人发笑的观点——妄图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终究只是饮鸩止渴,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