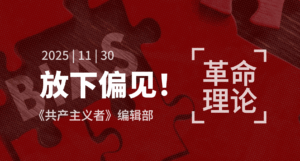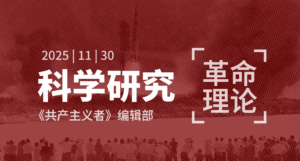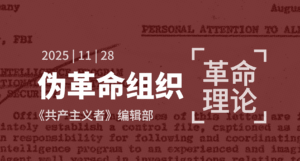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1.原始社会
约2500万年前,非洲热带雨林中出现了早期灵长类动物。根据最新古气候模型,中新世(2300万-533万年前)东非大裂谷的形成导致森林减少与草原扩张,迫使部分古猿下地生活。2025年对埃塞俄比亚地层的研究证实,约700万年前的地质运动加速了草原生态系统形成,促使南方古猿选择直立行走以扩大视野、节省能量消耗(直立行走能耗仅为四肢行走的25%),这种适应性改变并非基因突变的结果,而是群体行为通过数万代重复劳动形成的生物力学优化。
700万年前的非洲,南方古猿的直立行走标志着其与猿类的分化,也是人类进化的开始。2025年最新的基因研究表明,古人类脑容量的显著增长发生在距今约200万至30万年间,与旧石器时代工具的复杂化进程高度同步。劳动对智力的塑造具有双向性: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的石器工具显示,早期人类(如能人)已有意识制造工具,这种重复性劳动促使前额叶皮层发育,强化了计划能力和抽象思维。东非大裂谷出土的古人猿骨骼力学分析显示,手部骨骼构造的精细化早于脑容量爆发性增长约50万年,这证实了“劳动先行”的假说——即工具使用需求推动神经系统演化,而非相反。在认知层面,集体协作的狩猎行为催生了语言符号系统的萌芽。对欧洲尼安德特人喉部结构的重建表明,其发声器官已具备初步语言能力,而南非布隆伯斯洞穴发现的7.3万年前的几何刻痕符号,则揭示了抽象符号思维的出现。这些能力使得人类能够传递复杂经验,形成超越血缘关系的协作网络,为氏族社会的诞生奠定基础。
旧石器时代(约250万-1万年前)的采集-狩猎经济是全球原始社会的共同起点。非洲的桑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洲的克洛维斯文化均展现出相似特征:以氏族为单位的游群结构,平均分配食物,石器工具以打制为主。但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技术路径分化,例如在欧亚大陆草原带,猛犸象狩猎催生了投掷武器的精细化。在东南亚岛屿,竹器的广泛使用替代了石器的部分功能。而非洲热带雨林居民则发展出利用植物毒素的狩猎技术。这种技术多样性表明,早期人类认知能力本质是环境压力与社会协作共同塑造的适应性产物,个人技能完全依赖氏族代际传递的教育体系,北京田园洞人的石器制造技术需数十年学习周期即是明证。
新石器时代(约1.2万年前)标志着新的开端。西亚的“新月沃地”最早完成野生小麦与大麦的驯化,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与中美洲的玉米栽培出现。农业的兴起不仅带来定居生活,更引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显示,早期农业聚落已出现仓储设施和宗教建筑,剩余产品的积累催生了专职祭司阶层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大洋洲的塔斯马尼亚人因地理隔离未能发展出农业,其社会结构长期停滞在小型游群阶段,这印证了环境对技术传播的关键影响。此时的上层建筑仍以原始宗教和习俗为主,中国半坡遗址墓葬随葬品差异极小,证明存在尚未形成制度化的阶级分化。
所谓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原始社会基本单位,成员通常具有共同的祖先,通过母系或父系世系联结,其核心特征是血缘共同体;所谓部落,是由两个或多个血缘相近的氏族或胞族联合而成的更大社会组织,是氏族制度的高级形态。其核心特征是文化共同体,强调地域、语言和习俗的统一。6
有意思的是,氏族制度作为原始社会的普遍组织形式,在各大洲呈现出惊人相似性。西伯利亚的鄂温克族、北美易洛魁联盟和非洲班图人部落均实行氏族议事会制度,重要决策由全体成年成员共同商议。中国半坡遗址的墓葬考古显示,氏族成员随葬品差异极小,印证了“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生产关系特征。同时,良渚文化的玉器生产和两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均需数百人协作,个体劳动完全嵌入集体分工p体系。这种“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机制(如秘鲁Caral遗址的金字塔建造)表明,个人的劳动价值始终由社会关系定义,而非单纯的抽象的“自我实现”。这种平等主义并非出于道德自觉,而是环境压力与低水平生产力的必然选择:在平均寿命不足30岁、婴儿死亡率超60%的生存压力下,集体协作是维持种群存续的唯一途径,个体离开集体无法获取足够生存资源。而且,原始社会的知识积累(如制陶、用火技术)通过代际传递完成。考古发现显示,北京田园洞人的石器制造技术需数十年学习周期,个体的技能完全依赖氏族教育体系。这种技能再生产机制证明,个人的认知能力本质上是社会经验的具象化。
此外,现代研究表明,所谓“母权社会”更多是特定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选择,而非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母系氏族社会作为人类早期社会的普遍阶段,其核心特征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构建社会组织,世系与财产沿母系继承,但这一制度并不等同于“母权制”。后者特指女性全面垄断政治、经济及宗教权力的性别等级结构,而考古证据显示母系社会多呈现平等共生性质。例如,2025年《自然》期刊发表的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研究,通过古DNA分析证实了距今475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存在典型的母系氏族结构:遗址南北墓区分别对应两个独立母系氏族,所有个体均呈现单一母系线粒体遗传(北区与南区线粒体类型截然不同),而父系Y染色体却高度多样化,表明男性通婚后离开原生氏族,女性则终身留居本族并主导血缘传承。然而,该遗址的随葬品数量均衡、无奢华器物,且同位素分析显示社群依赖平等分配的粟作农业,均指向资源共有、无显著阶层分化的社会形态,而非女性专制统治的“母权制”。类似的平等性亦见于人类学记录的纳西族“阿注婚”母系社群(女性掌握家庭经济但无父权式集权)及欧洲铁器时代的母系遗传线索,印证母系组织可脱离性别压迫框架存在。
金属工具的出现(约公元前6000年)根本改变了生产效能。青铜器的使用使欧亚大陆的农业产出激增,而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土著居民则独立发展出铜器冶炼技术。生产力的提升导致两性分工固化:男性主导农耕与战争,女性转向纺织与制陶。这种分工差异源于生理特征与社会建构的双重作用——男性肌肉量平均高出女性40%,适于高强度劳动,但2025年跨文化研究证实,南非桑人等采集部落中女性贡献70%食物供给,证明“性别优势”是否能被“利用”非常依赖具体的自然、社会环境;父权制的真正形成源于剩余产品积累引发的继承权需求,而非生理决定论。
原始社会晚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个体劳动取代集体劳动,私有制由此萌芽。在其中,社会分工的深化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关键因素: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游牧部落从农业部落中分离,游牧部落的牲畜最早成为私有财产;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氏族首领在部落交换中逐步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加速了私有化进程。剩余产品的出现进一步为剥削创造了条件,战俘不再被杀死而是沦为奴隶;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也日益加剧,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对立由此逐步形成。私有制最终形成的标准包括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个体劳动普遍化、社会分工深化导致私有财产制度化、剩余产品积累引发占有关系变革。
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表明,专业工匠阶层已从农业中分离,手工业的专业化加速了剩余产品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积累必然引发占有关系的变革。在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时期(公元前4000年),楔形文字记录显示神庙开始征收农产品作为“神圣贡赋”,这实质是私有制的早期形态。中国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随葬猪下颌骨数量出现数十倍差异,标志着氏族成员间贫富分化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尼日尔河畔的杰内-杰诺遗址显示,铁器时代(公元前500年)的社区已出现围墙建筑,这种防御需求折射出资源争夺的加剧。也就是这个时候,阶级社会在逐步形成。阶级最终形成的标准体现为剥削制度化、贫富分化加剧导致阶级对立固定化、阶级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随着阶级矛盾激化,国家作为暴力统治机器也就产生了。原本服务于氏族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被贵族掌控,转变为镇压奴隶反抗、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恩格斯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非社会协调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游牧社会与原始社会晚期的根本差异在于其生产方式:游牧民族依赖流动性畜牧经济,牲畜的私有化更早且更彻底,这使其社会结构更易形成军事贵族主导的等级制,而非定居社会基于土地公有的氏族共同体。
奴隶制社会的形成:战争的规模化是阶级社会诞生的催化剂。苏美尔城邦间的资源争夺催生了职业军队,战俘成为最早的奴隶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奴隶制并非线性发展的必然阶段: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的“花环战争”虽捕获大量战俘,但主要用于宗教献祭而非生产劳动,这表明奴隶制的形成需要特定经济基础。同时,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诞生伴随着法律与暴力的制度化。汉谟拉比法典第15-20条明确规定奴隶买卖规则,而殷墟出土的带枷陶俑则证实了刑具的普遍使用。地中海地区的城邦国家通过公民权制度将奴隶排斥在法律关系之外,这种“人格否定”的法律建构,使奴隶制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
邦统主义社会的形成:在邦统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东亚,奴隶制并未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中,庶民以集体劳作形式依附于贵族土地,这种“众人”身份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邦统制社会的核心特征包括:土地国有制下的农村公社、专制君主对剩余产品的集中掠夺、以及臣民作为“普遍奴隶”的身份。印度种姓制度下的首陀罗阶层同样具有半奴隶性质,其形成与雅利安人征服原住民的历史密切相关。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也呈现出了这样特殊的发展路径。马里帝国的奴隶主要被用于投入王室卫队与手工业,而未被大规模投入农业生产;斯瓦希里城邦的奴隶贸易更多服务于印度洋贸易网络,这种外向型经济延缓了本地奴隶制的深化。这些差异表明,奴隶制的具体形态深受地理环境、文化传统与外部交往的影响。(邦统主义的问题会在其他文章论述,本文暂不深入)
封建制社会的形成:北欧日耳曼、东斯拉夫(俄罗斯)、日本、朝鲜、越南、吐蕃、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爱尔兰等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文明。
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制社会的可能性源于特定环境与技术条件下集约化农业对劳动力的高效组织需求超越奴隶制的大规模控制成本。当气候暖湿化扩展宜耕区域时,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发形成正循环,但寒冷期导致的农作物减产迫使自由农依附领主,加速土地兼并。特殊的地理条件也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例如北欧日耳曼部落面临冻土带开发难题,通过扈从制向采邑制转化,将公社自主地转化为领主封土,避免奴隶制低效;东斯拉夫基辅罗斯的森林草原环境限制大庄园经济,因而维尔夫公社可以经索贡巡行直接演变为世袭领地制,奴隶(霍洛普)仅占人口5%且从事家务;日本火山岛导致耕地碎片化,“部民制”的奴婢难以支撑农业主体,班田崩溃后的庄园制形成武士-本百姓的封建依附。这种转型本质是环境压力下原始公社解体与军事贵族权威结合的产物,如埃塞俄比亚高原干旱促使农耕公社接受“古尔特”分封,而吐蕃高寒区通过“庸”制将牧民固着于寺院庄园,从而直接实现封建社会。
2.奴隶制社会
“在奴隶制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特殊的所有者,是这些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完全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奴隶)人身,形成“工具化”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奴隶制中“劳动者本身作为生产工具被纳入生产资料范畴”(《资本论》),奴隶的劳动力再生产仅以满足最低生存需求为目标。这种绝对支配性使得其他经济形态(如自由手工业)仅能在奴隶主特许的缝隙中存在,例如古罗马的“特许奴隶工匠”制度,其剩余产产品最终仍被奴隶主用于购买更多奴隶或奢侈品消费,而非扩大再生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坦言:“我们不需要机械装置,因为奴隶就是最完美的工具”。像是希腊科林斯遗址出土的公元1世纪水力磨坊,因奴隶主抵制而废弃。
伊庇鲁斯战争后,罗马将整片地区人口贩为奴隶,恩格斯称其为“系统化的人肉掠夺”。这种掠夺规模在公元前2世纪达到顶峰,仅德尔菲神庙碑文便记载单次奴隶交易超3万人。奴隶生产极其浪费,它需要不断提供新的奴隶来替代受伤或死亡的奴隶才能存续。由于奴隶的生活环境恶劣,他们的自然繁殖非常缓慢,因此唯一真正的补充奴隶数量的方法是征服其他地区。
在奴隶制社会中,土地私有化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萌芽会被暴力扼杀。马克思指出,奴隶制经济要求“将劳动者本身作为可移动的财产”(《资本论》第一卷),这直接否定封建制所需的土地与农奴的固定依附关系。同时,奴隶制“用锁链而非契约维持劳动,这使得任何向封建依附关系的过渡都被视为对奴隶主特权的威胁。”(《反杜林论》)例如,古罗马共和国后期出现的“隶农制”(Colonatus)虽带有封建色彩,但奴隶主阶级通过法律强制将隶农重新贬为奴隶——西塞罗在《为凯基纳辩护》中宣称:“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彻底否定了隶农的人身权利。此外,奴隶主通过垄断市场(如罗马的“国家工场”制度)迫使自由工匠沦为债务奴隶,公元1世纪罗马政府颁布《佩特罗尼乌斯法》,禁止释放技术奴隶从事独立手工业,迫使自由工匠与奴隶竞争。
这里我们要补充一点:1790年至1863年的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与古典奴隶制存在结构性差异。前者深度嵌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以种植园为核心生产单位,通过奴隶劳动大规模生产棉花等商品作物,其产品直接供应英国及北方工业区的原料需求,本质上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奴隶主将利润投入土地扩张和奴隶再生产,形成以商品输出为导向的积累循环,这与古典奴隶制“消费优先”的掠夺模式不同。尽管同样依赖暴力强制,但南方奴隶制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资本积累,客观上推动了美国工业化进程,其经济逻辑已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尽管南方种植园为资本主义市场生产原料,但奴隶主将奴隶视为固定资产(如工具、牲畜),其“再生产”通过购买而非生育实现。马克思指出这是“资本主义表皮下的古代奴隶制僵尸”(《1857-1858经济学手稿》)。美国共产党理论家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重建》中揭露:北方资本通过贷款给奴隶主获取双重利润——既收取种植园贷款利息,又剥削棉纺织工人。这种“奴隶制-金融资本”共生体才是美国工业化的真正引擎。相比之下,奴隶制经济的本质是“消费导向型掠夺”,其生产规模扩张依赖战争俘获新奴隶,而非改进技术。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制度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特权政治分配。以雅典伯里克利时代为例,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官职向男性公民开放,公职人员通过抽签或选举产生,国家还为参政者发放津贴。然而这种民主仅限于约4.2万公民(占雅典40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将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完全排除在外。
奴隶制社会也存在一种特殊的统治模式:凯撒主义(Caesarism)。所谓凯撒主义国家,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化、个人独裁的统治形式的奴隶制国家。它源于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尤利乌斯·凯撒通过军事权威和政治手段颠覆共和制、建立个人独裁的历史实践,其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矛盾激化与社会转型困境的产物。凯撒主义的兴起,根植于古罗马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危机:土地兼并导致自由民阶层破产,同时奴隶与奴隶主矛盾激化,而传统奴隶主共和制下的贵族寡头统治(元老院)无法调和阶级冲突。这时,凯撒通过军事独裁与改革政策(如分配土地、扩大公民权),表面上以“超阶级”姿态调和矛盾,实则通过暴力机器(军队)和官僚体系重构国家机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除了西欧以外,在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只有在非洲西部的索科托哈里发国(1804-1903)存在过严格定义的奴隶制社会。索科托哈里发国由奥斯曼·丹·福迪奥通过“圣战”建立,全盛时期人口超1000万,奴隶人口达100万-250万。
索科托哈里发国的经济依赖奴隶种植园,奴隶通过战争俘获的非穆斯林构成(该国法律禁止穆斯林为奴,但是奴隶可以通过劳作换取皈依伊斯兰教的资格而成为自由民,甚至还有这种作为前奴隶的穆斯林进入政府高层的情况存在),奴隶们在军事堡垒(里巴特)周围的庄园生产棉花、槐蓝、可乐果、乳油木、谷物、大米、烟草和洋葱等作物,支撑国家税收、军事扩张和对外贸易。
到了1853年后,索科托的经济实际上依附英国。英国通过军事威慑迫使索科托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其开放市场并降低英国商品关税,同时索科托出口的棉花、谷物等原材料需以低价优先供应英国商人。英国殖民当局直接掌控索科托的海关和关税权,将关税收入用于支付英国贷款利息,导致索科托财政自主权丧失。因此,索科托原有的“吉哈德经济”循环被英国资本打断:奴隶生产的剩余产品不再用于军事扩张或奴隶再生产,而是被英国低价收购,转化为英国工业原料,从而为英国的资本增值服务;同时英国工业品倾销摧毁了索科托本土手工业,迫使自由民沦为英国商品的消费者。至此,尽管其奴隶制形式保留,但生产目的已从维持军事-奴隶制闭环转向为英国市场提供廉价原料。1903年索科托被英国军事征服后,其领土被并入英属北尼日利亚保护国。英国殖民当局强制推行“开放经济”政策,利用廉价工业品倾销摧毁当地手工业体系,使尼日利亚沦为英国原材料供应地,阻断其工业化路径。同时,殖民政府垄断对外贸易渠道,1954年尼日利亚70%的出口输往英国,贸易顺差积累的“英镑结存”被英国冻结,剥夺其自主发展资金。
最后,我们列举一些奴隶制社会的一些主要阶级:
(1)奴隶主。奴隶主是奴隶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其阶级本质在于对生产资料(土地、工具)和劳动者(奴隶)人身的双重占有。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定义,奴隶主将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其剥削方式是通过暴力强制直接占有奴隶的全部劳动产品。奴隶制的剥削不依赖市场交换,而是通过法律(如《十二铜表法》规定奴隶不得拥有财产)、暴力(监工制度)和意识形态(如斯巴达将希洛人视为“天生奴隶”)维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奴隶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将同类物化为生产资料”。例如,古罗马的种植园主(latifundia owners)通过战争俘获奴隶,将其投入庄园劳动,奴隶的衣食住行完全由主人支配。
(2)奴隶。奴隶是奴隶制社会的最低阶层,其阶级特征在于人身权利被彻底剥夺,成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被排除在法律人格之外,无法拥有家庭、财产或自由意志。雅典奴隶市场的铭文显示,奴隶的价格根据体力与技能明码标价。奴隶的劳动成果全部归奴隶主,其自身生存仅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限度为限。例如,加图在《农业志》中建议奴隶主“给病弱奴隶断食”,因其丧失劳动价值。奴隶起义(如斯巴达克起义)虽可以动摇奴隶制,但未能建立新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奴隶缺乏阶级意识,“他们的反抗是绝望的反抗,而非新社会的助产士”(《哲学的贫困》)。
(3)自由民。自由民基本上是奴隶主、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和商人)和无产者(这里指没有土地或生产资料,主要靠出卖劳动力(如打短工)或领取城邦救济(如古罗马的“面包与马戏”)为生的群体,而非资本主义下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描述封建社会时有描述,因此这里不重复。
3.封建社会
“中世纪社会:细碎的小生产,生产机关适于个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细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为生产者自己所占有。生产是为供给生产者自己或其封建领主之直接消费。消费以外的剩余生产品才拿去出卖,才拿去交换;商品生产尚在初生状态。”(《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西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经济在3世纪后陷入危机。奴隶主庄园(latifundium)的扩张导致小农破产,奴隶因对外扩张停滞导致来源萎缩,劳动力短缺加剧了大庄园经济的困境。日耳曼人在匈人西迁与气候寒冷化的双重压力下南迁,加速了西罗马的崩溃。公元481年到843年,日尔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在西欧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马特推行采邑制,将土地连同劳动者分封给军事贵族以换取骑兵服役,形成领主-附庸关系。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分析,这种“以土地服役为纽带的等级制”取代了罗马的中央集权体制。自由农民因战乱和赋税压迫,被迫将土地献给领主换取庇护,逐渐沦为农奴。8世纪《萨利克法典》规定杀害半自由民的赔偿金远低于自由民,体现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法律固化。
加洛林王朝建立后,其封君封臣制度完善了封建结构。查理曼颁布《庄园敕令》,规定领主对庄园内农奴的司法权和劳役要求。农奴制度的确立创造了更稳定的生产环境:农奴获得份地的世袭耕作权,可保留部分剩余产品,刺激了农业技术改进,但需承担劳役及继承税,领主可随时收回土地;三圃制轮耕与重犁推广显著提升了土地利用率,推动农业生产力复苏。这与奴隶制下破坏性地使用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封建主通过土地垄断和超经济强制(如农奴人身依附)实现剩余价值榨取。马克思以西欧庄园经济为例,指出“封建主将土地分割给农奴耕种,以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形式占有剩余产品”(《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模式下,即便出现早期工商业(如中世纪行会),其生产仍受制于封建地租逻辑。例如14世纪佛罗伦萨毛纺织业中,尽管出现包买商制度,但佛罗伦萨毛纺织业的利润多用于高利贷资本输出(如向英王爱德华三世放贷),而非用于资本积累以扩大纺织业的再生产。这反映出封建生产关系对其他经济活动的“价值导向扭曲”。
在14-15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经济的封闭性与农奴制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商品经济发展。此时地中海沿岸兴起的城市工商业打破了自然经济结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商人通过远程贸易积累起货币资本,形成早期资产阶级雏形。
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使16世纪欧洲白银存量增长五倍(《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价格革命导致西欧实际工资下降40%,加速了土地贵族向资产阶级转化。18世纪英国议会通过系列《圈地法案》,至1800年约半数耕地被圈占为牧场,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述的“羊吃人”现象,正是马克思强调的“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编年史”的原始积累过程(《资本论》第一卷)。同时,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使棉纱日产量提升近百倍,彻底变革纺织业。1835年英国铁路里程达471公里,形成全国性市场。这种“劳动资料转化为机器体系”的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物质技术基础。
此外,随着海外殖民扩张和国内市场整合,区域性方言逐渐演变为标准民族语言,印刷术的普及强化了文化认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促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地区结合为具有统一政府、统一法律的民族”。荷兰联省共和国通过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将商业资本积累与民族意识觉醒相结合,建立了首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与此同时,绝对君主制的建立成为这一转型的政治枢纽。16世纪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王权通过“朕即国家”的集权政策,瓦解封建领主的军事特权,建立常备军和官僚体系。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中表示绝对君主制是“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权力”,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它统一度量衡、废除内部关税、对商业航行的保护等,使全国性的市场得以形成。另外,如英国都铎王朝通过宗教改革没收教会地产进行拍卖的行为,加速了土地资本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君主制是欧洲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央集权政体,其本质是封建贵族和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平衡上(这种阶级力量的平衡使绝对君主制具有内在脆弱性),对过去封建割据的逐步瓦解。例如,法国路易十四通过《南特敕令》废除贵族军权、建立常备军,并通过重商主义政策扩大税基。在过去的典型封建制度下,贵族通过等级会议(如法国三级会议、英国议会)享有分权制衡的协商机制,形成统治阶级内部的有限民主,而绝对君主制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虽在短期内强化了国家机器,却因剥夺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权而激化了矛盾。当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壮大后,必然要求自己掌握政治权力,从而容易导致政权更迭,而法国大革命便是明证。同时,君主为维持集权与战争(如路易十四时期国债达30亿锂),加剧了财政危机和阶级对立。这种集权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像是英国都铎王朝《航海条例》即为保护商业资本。
除了西欧的“典型封建模式”外,日本的封建制度也提供了与西欧并行的典型案例。中世纪日本的社会基础同样是细碎的小生产单位,德川幕府时期约70%的土地被大名领主占有,25%为幕府将军直辖,天皇与神社仅保留不足1.2%的土地,农民则被束缚在平均不足5反(约7市亩)的份地上,以实物形式缴纳高达60-80%收成的年贡。这种剥削模式与西欧庄园劳役地租本质相通:剩余产品首先满足领主消费,仅有少量进入交换与流通。日本庄园制的发展始于奈良时代对唐代邦统制下的均田制的模仿失败,天皇政府在743年《垦田永世私财法》承认垦荒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类似西欧的封建领地。但日本庄园通过“寄进”形成了独特的等级结构:在乡领主将土地进献给权贵(领家),领家再进献给皇室或摄关家(本家),构成“预所-领家-本家”的垂直依附链,维系这一体系的是年贡的层层分割。
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推行“检地政策”,确立“二公一民”税制(农民保留1/3收成),使小农获得较稳定的生产预期,刺激了肥料使用与水利建设。这与加洛林庄园农奴份地世袭化的作用类似,但日本的地主-佃农制也有和西欧封建制不同的地方:新兴地主虽掌握全国1/3土地,法律上仍从属封建领主,其剥削所得常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而非生产投资。德川幕府为维护封建基础,1643年颁布《禁止土地买卖令》,并多次强制外出务工农民返乡,阻碍了劳动力的商品化。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日本存在“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其领主世袭特权与西欧庄园制本质相通。日本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天皇-幕府-大名”的重层权力格局,天皇作为宗教象征缺乏实权,幕府将军虽掌控国家机器却无法完全压制地方势力,而大名则在其藩领内拥有独立的军事、司法和财政权,甚至能世袭领地并豢养效忠于私门的武士集团。这种分权催生了日本贵族等级内部的协商机制,例如江户幕府的重大决策需通过“老中会议”协调亲藩、谱代、外样三类大名的利益,而藩政改革时期长州藩的“村田清风体制”更允许中下级武士参与藩政讨论。同时,权力分散使统治者难以独断专行:1701年赤穗藩主被幕府处死后,其家臣为履行对藩主的忠诚义务,不惜违抗将军法令刺杀幕府重臣,此事也凸显武士的效忠对象分散于多重领主,这种法律与伦理的“冲突”本质上也源于封建社会权力结构的碎片化。
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出现在锁国末期(19世纪初)。畿内地区因棉纺业扩张导致粮食短缺,农民普遍“购米售棉”:大坂平原农村从北陆、九州购入大米,同时向江户输出棉布,形成跨区域贸易网络。濑户内海地区人口在19世纪增长1.4-1.9倍,长州藩等地的中下层农民也卷入商品生产。手工业方面,足利棉织工场已拥有30-200台织机,桐生丝织业带动人口百年内增长三倍,全国雇佣10人以上的工场从1854年的300所增至1867年的400余所。这种工场手工业虽具资本主义萌芽性质,却受封建价值体系扭曲:商人利润多用于购买武士身份或土地权利,而非扩大再生产。正如大坂商人贷款给大名的年利息相当300万石大米,远超工商业积累规模。
到了近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危机因内外压力加剧。1837年大盐平八郎起义号召“平均世道”,四万人参与的近江暴动摧毁土地清册,显示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同时,西南强藩通过“藩政改革”局部突破旧制度:长州藩1838年减免租税、采用洋枪并奖励西学;萨摩藩发展琉球贸易与蔗糖专卖,建立西式海军。这些改革虽以“富国强兵”为名,实则推动地方经济自主化,为倒幕运动奠定基础。当美国佩里舰队1853年叩关时,建筑在年贡剥削上的幕藩财政早已崩溃。19世纪40年代幕府年均赤字70万两金,萨摩藩负债达500万两,封建制度最终在内外夹击下被瓦解。
最后,我们列举一些封建社会的一些主要阶级:
(1)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通常拥有或部分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如自耕农),或租种他人土地(如古代的雇农)。农民阶级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生产,经济形态以自给自足为主,很少参与市场交换。
农民从来都没有过充当一个独立的革命阶级的作用。农民,就其客观利益来说,是社会革命的力量,但政治上是分散的和软弱无力的,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政党。农民的劳动方法相同,但是他们的劳动方法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农民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农民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纯粹的农民起义的结果都是被镇压而失败或是用新的前资本主义王朝来重建过去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农民才能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农民内部分不同的阶层(关于邦统制村社成员和邦统国家佃农,我们已经在论述邦统制社会时论述过了),如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雇农在古代是农民阶级中的无产者阶层,近现代是工人阶级,贫农则是半无产阶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半无产阶级包含贫农、小手工业者、小贩等,其特点是有极小生产工具但需出卖部分劳动力。”),中农、富农则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近现代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贫农很容易堕落到雇农的地位,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富农有成为地主或是资产阶级的潜力,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他们容易支持资产阶级。中农则是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
在封建社会中,主要的生产者是农奴,其阶级地位体现为对领主的人身依附与半自由状态。农奴可拥有工具、家庭和份地使用权,但不得离开领地。英国《末日审判书》(1086年)记载,农奴需缴纳“继承税”才能延续份地耕作权。农奴需无偿为领主耕种直领地(demesne),并缴纳各种杂税(如磨坊使用费);领主法庭可对农奴处以体罚(如砍手)、罚款或监禁。13世纪法国博韦地方法规规定,农奴未经许可结婚需缴纳“婚姻税”。另外,农奴逃亡(如德国“空气使人自由”法谚)和起义(如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也可以推动封建制瓦解。恩格斯指出,农奴制被破坏后,“进入历史的第一个资本家阶级是由被解放的农奴组成的”(《反杜林论》)。
(2)封建主阶级。在封建制度下,领主通过采邑分封获得世袭领地和司法特权,其权力并非完全源于君主的授予,而是基于封建契约形成的双向义务关系。例如,领主需向君主提供骑士武装和赋税,而君主则承认领主在封地内的自治权,这种关系使封建领主能够与君主形成某种制衡,从而出现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权力分层结构。因此,封建制下的权力结构是网状分权的,君主、领主、教会共同构成了制度上的多元平衡。
封建领主与教士阶层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双重支柱,其权力根基在于对土地的垄断性占有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赋予。封建领主通过采邑制将土地分封为世袭领地,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之上,以劳役地租(如每周三日为领主耕地)、实物地租(收成的三分之一)和货币地租(如英国“盾牌钱”)等形式被剥削剩余劳动。领主不仅掌握经济权力,还通过庄园法庭行使司法特权(如初夜权、遗产税),形成“司法权与土地权的合一”(马克思《资本论》)。作为封建主阶级的神权代表和大地主,教士阶层本身即拥有并管理着大量教会土地并征收什一税,将神权与地权紧密结合;他们运用宗教教义与仪式,系统地论证封建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将其塑造为“上帝意志”的体现,从而为整个封建主阶级的统治提供关键的精神支柱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保障,并通过垄断教育、婚姻与丧葬仪式实施精神控制。同样作为封建主阶级武装力量核心的骑士阶层,本质上是领主土地分封制度下的军事附庸,其基础在于领主的土地授予和农奴劳动供养,职责是提供武力保护并维持封建秩序。领主与教士的联盟在十字军东征中达到顶峰:骑士阶层作为封建主阶级的军事延伸,以宗教战争名义进行领土扩张,教会则借机攫取东方财富。但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瓦解了这一体系。货币地租的普及使农奴得以赎买自由,城市行会的兴起挑战了领主的司法垄断,宗教改革则打破教会的精神独裁,最终催生了“脱下袈裟的资产阶级”(恩格斯语)。
(3)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手工业者(例如行会师傅)、小店主、自由职业者、上述的资本主义中的中农和富农、小工业家、小商人等,都是小资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小资产阶级包括小生产者、小业主,其经济地位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此外,列宁还说:“小资产者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种双重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动摇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封建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其具体组织形式是封建行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职业组织),其内部关系以等级制(师傅、帮工、学徒)为核心,而非基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关系。行会师傅拥有作坊、工具和原材料,同时以家庭劳动为主,可能雇佣少量帮工或学徒,但剥削程度有限(学徒以学习技能为目的,而非纯粹剩余价值剥削)。如马克思所说:“行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而是一种宗法关系……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工资,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将来也能成为师傅。”(《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另外,行会师傅受封建行规束缚(如产量限制、价格管制),缺乏资本积累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