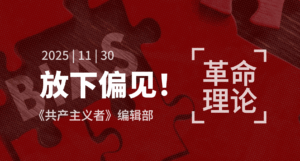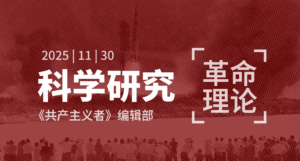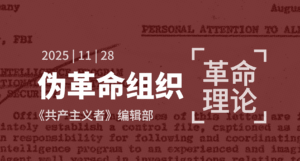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事件详情
2019年6月香港,当一名为梁凌杰的35岁男子从太古广场堕楼身亡后,正式宣告了抗议示威行动进入暴力阶段。没有人会预料到事态的发展会在此后恶化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一场发生在香港的“反修例暴动”,已经成为了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场庞大的社会运动,我们同志们或许会为这样的社会暴动的偃旗息鼓扼腕叹息,认为这场运动的失败是革命浪潮的退却。其实事实恰恰相反,这一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相悖的,甚至它是打着“反社会主义”的旗号而进行的(尽管参与运动的大多数香港人并不知道他们反对的“社会主义”严格意义上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在形式上,更是向我们展示了完全错误的运动实践和斗争路线,而这决定了它必然走向衰亡和失败。同时,这场运动又反映出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博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不同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和激烈交锋,可以说,这场失败的运动唯一的价值,就是给我们革命的同志上了活生生的一课——我们应该如何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一切都要从一位名叫陈同佳的香港籍男子开始说起,概括地说,他同配偶在台湾旅行途中,残忍将配偶杀害肢解,并放到行李箱里。而当真相水落石出,他已经潇洒离台,回到香港。此时一个从来没人留意到的法律漏洞开始捉弄世人——港台之间并没有白纸黑字、具有明确法律效应的引渡条例,也就是说,只要陈同佳本人足够懦弱以及足够没有担当,永远也不离开香港,那么台湾警方和香港警方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香港政府果断拟出逃犯引渡法案,欲补上这个法律漏洞。这个过程听起来非常合乎逻辑,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个法案——它的引渡地区包括中国大陆。
“香港众志”率先发起静坐抗议,其后“民间人权阵线”组织了数次示威游行,要求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并表达了对中国大陆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担忧会发生不公平审讯的事件,危害“一国两制”以及香港在《基本法》下司法独立的管辖地位。但是香港政府并没有对此有积极回应,同年6月继续在立法会恢复二辩。6月12日,正当香港立法会里“亲中派”和“仇中派”唇枪舌剑的时候,示威者在外不断丢掷杂物,试图阻止程序进行,并首次和香港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同日,香港警方正式将示威运动定性为暴动。双方开始长达一年多的暴力对抗,示威群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
- 完全撤回条例修订
- 撤回暴动定性
- 撤回对示威者的暴力定罪
- 追究警队滥权
-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下台
同时,暴动群体开始有规模地组织起来。在现实运动中,他们开始统一着装(黑衣,护目镜,黄色帽子等),呼喊相同口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网络上,他们开始统一宣传路径,建立自己的社交平台,其中一些群组被用作情报传递和各地区暴动组织之间的实时交流。其后,示威运动变成街头政治的暴力行动,他们开始有组织有预谋地破坏城市的基础设施,阻碍日常社会运作,包括但不限于阻碍地铁运行,阻塞马路交通等。事态发展的其中一个极度恶劣的影响,就是把香港社会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彻底撕裂开来——在一个家庭中,年轻一代和长辈一代因为政见不同开始敌对(存在关系彻底破裂的情况,甚至导致暴力冲突,青年人自杀等);在社会上,群体开始分成两大派别,一派是“黄丝”,即仇中派;一派是“蓝丝”,即亲中派,不论职业、性别、民族、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甚至是阶级,整个社会开始迅速进入“分类标签”的过程,两大阵营在互联网、在现实中以各种形式展开激烈言论斗争,暴动群体和警察的暴力冲突随着时间的发酵在整个香港社会中泛化发酵,逐渐发展成一般市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仅仅只是因为政见不同,普通市民甚至可以在街道上大打出手,甚至可以置对方于死地;这种失控的社会情绪同时也以最猛烈的姿态占领了教育机构,大学和中学的青年人对此极为狂热,纷纷以“罢课”和“筑人墙”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以香港理工大学的“理大围城”最为出名。在港区《国安法》出台之前,暴动组织长期在基层占据舆论优势,他们以各种手段吸纳人员:不断重复诉求口号、创造所谓的内循环“黄色经济圈”、建立自己的舆论媒体从而大范围传播有利于暴动的信息。议会斗争毫无疑问也是风暴中心,以“民主党”为首的仇中派和以“民建联”为首的亲中派也在互相攻讦,在立法会上一齐恶语相向,丑态百出。
事情的转折点最开始出现在《禁口罩法》的迅速出台,由于暴动组织全副武装统一用黑色布料遮住了面部,因此当他们使用暴力攻击警察或者是路边偶遇的政敌,甚至只是无辜的扫地工人,所造成的伤亡没有办法追究(但是他们会在被捕时向周围同伴呼喊自己的个人信息,这是因为当时他们统一认为在被捕后会被警方“不透明处理”);暴动维持到2020年后进入新冠疫情阶段之后烈度有所减却,时不时会出现的集会依然时常让“五大诉求”的口号充斥在整座城市的空气里,路边建筑被暴动组织用喷漆写上各种不堪入目的、粗俗的针对警方的标语,同时也有大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仇恨标语。所有的活动在2020年7月1日港区《国安法》出台以后迅速偃旗息鼓,随之出现的是,大部分在运动中的“精神领袖”,有的例如黄之锋等,被迅速清算拘捕入狱;有的例如罗冠聪等,早已溜之大吉逃亡海外,寻求外国政府的政治庇护。“国安”的政治正确迅速凌驾“反共”的政治正确,整个香港社会也刹那间进入一种很诡异的氛围当中,热暴力开始变成冷暴力,在《宪法》的政治权力的绝对暴力之下,街头政治暴动迅速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香港人开始进入一种类似刘慈欣笔下的“黑暗森林”的时代,每个人之间开始忌讳、害怕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大家十分有默契地开始避免谈论有关话题;街头暴力被压缩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经济上,黄色经济圈依然在灰色地带中,暴力被符号化,通过一些卡通图像、口号缩写来展现,比如相关群体会拒绝搭乘港铁,只光顾相同阵营的店铺等。同时,所谓的“中产阶级”大吐苦水,认为末日降临,《国安法》的实施在他们眼里比《逃犯条例》还要洪水猛兽,因此大量“中产”开始批量移民,逃离香港。同时,国安教育正式开始纳入教育体系,不过其手法非常拙劣,基本不涉及详细的历史教育,只停留在表面形式的科普(简而言之,就是只宣传现代科技经济成就,但是不注重中国的历史教育,尤其是革命历史的教育,下文会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阐述)。自此,轰轰烈烈的“时代革命”,正式寿终正寝。
屁股决定脑袋
这是一场错误又幼稚的政治暴动,不论他们所谓的领袖用如何漂亮的字眼作宏大修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都不能掩饰其反动的本质,我们许多同志或许会看到他们举着“反独裁”的旗帜,便认为他们是进步的,事实则恰恰相反。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资本主义,是因为现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背叛了它的人民,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权贵官僚的集团,它已经成为了满足统治阶级需求的利益集团;而暴动群体的“反共”,则是彻底地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甚至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一窍不通,普遍对共产主义抱有严重偏见。因此整场运动,以微观视角来说是思之令人发笑又无奈的:他说的“马”不是“马”,你反的“共”又是什么“共”?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政治运动,因为所有前置条件决定了它的暴毙的必然:它首先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主导这场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只有一个,就是“反共”。但是为什么反共,理由就五花八门:
基数最大的就是源自于对共产党的偏见和非常偏颇的印象,他们直接将共产党和“不民主”、“专制”等字眼扯上关系,同时,这群人必然是在香港生活成长的,内心带有对这座城市天然的、不可蔑视的自豪感,甚至是自傲感。他们认为香港是一座成功的城市,满足所有现代的普世价值要求(民主、自由等),并且一致认为这种成功和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关系,反而和英国殖民政府有关系,他们内心天然带有对中国大陆人的鄙视,这种鄙视深刻到教育、文化和整个社会环境中。相比很多去过香港的同志们都感受到,你使用粤语或者英语相比于说普通话,受到的待遇是天差地别的。因此,他们响应运动的情感最为朴素,就是担心“中共恶魔”借着《逃犯条例》把大手伸到香港,破坏一国两制和香港独立的司法制度,公报私仇抓捕政治犯。这个群体的情绪也最容易被煽动的,历史知识的来源基本上是Youtube的媒体宣传,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这群人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泛新自由主义,他们非常认同自由市场这一套,毫不夸张地说,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出厂设置”,他们打心底里不相信市场是可以被计划的;他们认同普世价值,又承认竞争和不平等的存在合理;他们不希望政府对市场交易有过多干涉,又要求政府对经济活动兜底,提供各种补贴,但是他们自己或许不会知道自己的意识形态是这样子的,他们只是天然地对这一套东西表示认同,并觉得这是人类社会天然的属性。也就是说,运动中最庞大的群众基础,打心底里就瞧不起他们以为的”共产党”的那一套。这种意识形态就像炸药一样一点就爆,促使他们迅速投入暴动当中,并且通常是手段最为极端的一类,他们直接在前线使用暴力,丢掷燃烧瓶、抢夺警员枪械、路上一旦抓住政见不一的人就围殴等。这不是激进,而是无组织、无目的、无思考的莽夫式倾泻。
另外一种“反共”的理由纯粹是从一个帝国主义倒向另外一个帝国主义,也就是以民主党为首,和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买办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他们因为服从了美帝国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统治,因此执行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意志。他们的任务自然是替美帝国主义者在香港充当意识形态代理人战争的先锋,宣传美帝国主义者的阶级意志和所谓的美帝国普世价值观,并负责在香港议会尝试夺取政治主导权,帮助美帝国主义者在香港组织政治暴动。不过,反动属性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这群人身上得到最为精彩的展现。在暴动初期,可以看到这群人不断在各种媒体上抛头露面,向社会和世界倾诉自己的政治诉求,却鲜少看见他们切实参与到暴力冲突当中,而且,有极大一部分来自这一群体的人,借此机会大肆敛财:要么是美帝国主义者的奖赏和“辛勤工作”的报酬,要么是暴动群体的自发筹集的“政治献金”,具体有多少真的应用在政治活动上,几乎无人知晓,也无人追查,只知道在《国安法》杀出来后,不少人早就跑路逃亡到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以”媒体喊话“的方式支持香港的”革命“。因此,”反共“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门生意,正如姜文在《让子弹飞》设计的台词一样,张麻子脸上长没长麻子根本就不重要,人们相不相信张麻子脸上长麻子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否真的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邪恶独裁,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任务必须完成——让香港人深信中国共产党就是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者。(可悲的是,尽管对于他们来说中共的真正成色不重要,但是中共也确实越来越专制反动了,而且它做到了连资本主义都做不到的事——后者是形式上是人人民主自由,内容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后者则是形式上无产阶级民主自由,内容上却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最后一类最为特殊,需要结合历史辩证唯物地看待——他们就是在上个世纪末期因无法忍受中共的政治压力、或是因为中共落实到地方政策出现极端偏差而遭迫害的知识份子,或者是地主阶级后代、本就属于反动分子的后代。这群人基本上可以视为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和“毛派”在基层分庭抗礼的群体,特征是蛊惑性极高。这一群体无非是在“文革”后期拥抱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发表意见能力上比一般劳动阶级要高出许多,但同时他们又打心底里不认可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忍受“知识分子要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要求。因此,他们对于时代和中国共产党的描述,又是另一种偏颇:他们只强调自己遭受了什么样的迫害,却避而不谈自己所处的阶级是对于劳动人民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这里甚至可以衍生出一个题外话——那就是知识分子从来不肯真正俯首为人民,是千百年来专制主义王朝时代留给中国人民的万恶隐疾。由于他们在阐述事件和历史的过程中通常会避免谈论马克思主义,而只谈论事物发生的表面情况,也从不肯深入剖析矛盾的辩证发展,这就给了香港人(其实也不止香港人)一种感觉——当年的共产党对人的压迫真是太过分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万恶之源,因此一定要抵抗赤色入侵。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路线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也不清楚中国大陆实际的社会情况,许多人就是被知识分子片面的主观描述所蛊惑,从而造就了对共产主义严重的偏见。而地主阶级的后代就更不用多说,其反动性质根本从头到尾就没有变过,许多他们的后代将这种仇恨在香港延续下去,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分辨清楚,这一部分群体是与我们同志有强烈的“阶级仇恨”的,在绝对的立场上,我们不可以有任何退让的可能,必须与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那么为什么这种“反共”不能使他们的暴动成功呢?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不能使他们绝对团结到真正的革命队伍——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所自带的软弱和投机,使得这个队伍没有面对政治权力的暴力镇压的抵抗能力。首先,他们的意识形态只是纯粹的“反共”,所谓的“反共”背后,主要的诉求就是普选,这暴露了整场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导——不过是美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西式民主“,也就是所谓的一人一票式民主,实则完全忽视了这根本只是个形式,关键在于统治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成色。从而,这群人真正想要的其实是生活当中各种方面的无政府主义,甚至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新自由主义变种——他们渴望在日常的市场投机活动中,政府不能有任何程度的插手,但是在福利方面却又对政府有极高要求,而且同时又要求政府承担任何来自市场的风险,给所有人兜底,这实际上是极度自私的表现。这种深埋在他们心里的种子,被他们用看似宏大光明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所包装,实则正是因为这种自私,促使他们厌恶接触劳动人民,注定了他们建立的所谓的“革命队伍”,不会沉下心来接触劳动人民。相反,他们会无视劳动阶级的真正处境,强行输出自己的“革命意识形态”,并试图绑架劳动阶级——例如阻碍地铁运行,强迫广大劳动群众同他们一起投入“革命”,但凡劳动阶级对此表示抗拒,他们动辄就要打要杀。但可笑的是,尽管他们在香港闹了一年,但是香港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吃不起饭,交不起房租的事,社会运行尽管缓慢但并没有彻底瘫痪,这显示了参与暴动的群体本质上是和劳动人民脱离的,他们甚至不承担社会运作的主要关键程序。马后炮来说,抛却群体里面那些学生,从暴动后大规模中产阶级移民的现象可以看出,这群人的成色也不过如此——自以为掌握社会运作本质的小资产阶级,实际上他们每天所做的只是加速了货币流动、并没有进行实际物质生产的市场投机行为。没有了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取而代之的是反动又落后的新自由主义,促使他们亲手将最应该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一步一步推向他们的对立面,而这也就注定了这场所谓的“时代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而那些帝国主义的傀儡就更不用多说了,他们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那就是从头到尾都必须服从帝国主义的意志了,辩证来看,香港不过是中美两大帝国主义博弈的棋盘,一旦棋局胜负已定,棋子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美帝国主义者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战略部署将重心从香港转移出去,但是重心一旦转移,那些帝国主义傀儡就会如丧家之犬般四处乱窜寻求庇护,这也是为什么像罗冠聪这样的帝国主义傀儡在暴动被镇压后火速离港,无力建立自己的政党,只能寻求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庇护了。至于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后代和地主阶级的逃港后代,它们本身就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从一开始没想着要为人民服务,其投机的属性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香港有大量穷苦劳动人民还在忍受“鸽子笼”一般的居住环境,许多穷苦人民还在靠着政府的微薄救济艰难生存。从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一个改革人士,愿意投入到解放这些穷苦人民的工作当中,甚至是那些区议员,它们所渴望的只是那些人手里的选票,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私利。纵观完整个暴动群体,可以发现这群人基本上完全脱离真正的劳动阶级,甚至将劳动阶级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强迫劳动阶级接受他们的“革命诉求”,强迫他们加入革命,如果不加入,就会被他们暴力清算,这无异于自取灭亡,将革命成功所必须要团结的有生力量抛弃,这就是所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通病,这种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的、落后的、反动的政治运动,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
小孩子过家家
其次,这场政治暴动的具体实践,也是幼稚到令人发笑的程度。这场反修例的政治暴动从策划到实行,只有短短半年时间,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纯粹的情绪使然,直到暴动开始才匆忙地一步一步规划运动组织。
整场暴动从头到尾停留在“街头政治”阶段,离武装暴动差了十万八千里,甚至连警察这一道防线都没击溃。武装暴动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运作、良好的队伍纪律、科学的理论指导、统一行动思想、以及训练有素的革命成员——这些全部都没有。暴动群体的组织运作十分涣散,他们的目的是阻止《逃犯条例》的通过,随着暴动的开展又变成了“真普选”,在议会斗争失败后,这群人迅速倒向了“街头政治”,妄图通过破坏城市基础设施,阻碍社会运作从而使政府让步。这展现了新自由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通病,那就是要“速胜”,严重缺乏持久战的恒心,在议会斗争失败后,他们不会想着团结劳动大众,把他们的利益诉求结合到劳动阶级的利益诉求,忽视了劳动阶级的生存处境,而只是自顾自地搞“革命”。在暴动中,暴动群体并没有展现良好的纪律性,经常会因为个体情绪化而催生失控的局面,最常见的就是部分暴动成员会把无辜的路人也纳入攻击范畴,无差别武力审讯路人等。同时,群体内部也思想不大统一,在暴动中期,内部也意识到有些人的行为已经彻底过线,这不利于暴动组织在国际上的舆论,因此又诞生了“勇武派”和“和理非”两大派别,简单来说,前者负责干暴力的勾当,后者负责在媒体镜头前给暴动组织洗地,两大派别有时逢场作戏互相批评,有时又惺惺相惜互相鼓励,好不诙谐。在行动思想上也不统一,示威游行漫无目的,只是遇人就抓来审讯一遍,遇到能打砸的设施就打砸一遍,整个过程和流寇没什么区别,甚至发展到后期有恐怖主义的色彩,暴动群体越发歇斯底里,眼里容不下任何政见不一的人士。
其次,就是没有做好群众工作。任何革命的有生力量都绝对是广大劳动人民,因为是广大劳动人民掌握的社会运作的核心本质,没有劳动人民的生产,就没有社会的运作,而一个社会的正常运作是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显然,暴动群体的麻雀小脑不支持他们思考到这一步,他们不思考如何将自己的诉求——抗议《逃犯条例》,和劳动人民的诉求——生存,结合起来。事实上,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这场运动的失败和可笑,因为广大劳动人民的第一诉求是更好的生存,中共来不来抓人和他们没有半点关系,他们只是想要更安稳的工作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也就是说从一开始,“革命”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本来就是不重合的,自然劳动人民也不会有投入革命的热情。但是,如何处理利益矛盾不重合的情况,本来就应该是革命队伍所要花时间去研究、考察、设计的,结果这群革命队伍不但没有设计,也没有考察,说革命就革命,还不是扛枪,只是随便乱丢燃烧瓶,每天早上都站在地铁闸门不让人上班,不但没有做好组织群众的工作,反而还阻碍了群众的工作和生存,成功的做到了由二者利益不重合转变为二者利益相违背,仔细想来如何不令人“拍案叫绝”?这就给我们的同志一个很大的启发,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如今无产阶级还没有绝对的革命热情,他们依然可以通过工作实现自己的生存,因此我们绝对不可以走他们的老路:急于革命,强迫群众加入,忽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相反,我们一定要不断思考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以及如何将这些矛盾利用起来,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时刻铭记,我们必须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无论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要求劳动人民替我们牺牲任何东西,相反,我们要鼓励群众,带领群众去夺回属于他们的劳动成果,从来只有革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没有人民服务革命共产党的,倘若如此,那么我们的革命就和这些自私自利的暴动没有任何区别了。
一叶知秋
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会允许笔者就恰此停留在这场运动的表面上,事实上这场运动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有关这种奇妙的城市的一些特别信息。首先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历史是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动态的,事物不会是永恒不变的,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的。它不仅有殖民的历史,也有革命的历史,它有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色,又包含了深远的中国文化底蕴,因此我们不能随意将香港的一些情况同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其他社会作类比,生活在这种城市里的人,通过他们实际的物质生产的生活,创造了属于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至少曾经是),产业结构在20世纪末就已经完成了由工业到金融的转型,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行,中资和外资首先集中在香港这一个窗口进行融合交流,而这也将大量热钱带到香港,投资的热潮首先带动了香港的金融产业,从而金融产业又通过货币交易的各种手段带动各种服务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20世纪末的香港是一片繁荣昌盛,许多人会有一种错觉——那就是香港十分依赖旅游业,其实事实恰恰相反,旅游业只不过是香港文化影响力的物质体现,其本身带来的货币效益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影响力吸引来的投资。同时,作为中国在初步迈入世界市场的唯一同世界贸易市场交流的窗口,香港又很自然地承担了转口贸易的角色,因此香港这座城市所依赖的收入来源,并非旅游业,而是全球的转口贸易市场以及各种来港的投资,香港政府之所以能长期提供较高水平的福利,正是因为有这样充足的收入。为什么要在这篇文章提到这一点呢?是因为2019年的这场暴动,引发了一个很“山体滑坡”的结果,就是港区《国安法》。
“街头政治”由于手段不在武装暴动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而是十分幼稚地通过打砸来逼迫政权妥协,无数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是作茧自缚。我们可以看到港区《国安法》出来以后,暴动瞬间偃旗息鼓,相关人员作鸟兽散,暴动群体土崩瓦解,这告诉了我们幼稚的街头暴动面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暴力之下,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另外,为什么前文会说到这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博弈呢?因为2019年恰逢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末尾,在此之前,贸易战争已经开打。我们马后炮地从结果推论,港区《国安法》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使投资对香港市场失去信心——这牵涉到了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共产党所有关的一切企业机构的不信任,但其实大部分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的敌对,那只是他们冠冕堂皇的修辞,他们只是担心自由贸易被政治权力随意介入,如果共产党从来不介入,他们是不会有意见的。但是香港是中国对外货币博弈的一个关键地区,中国可以通过香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挑战美元霸权。因此,通过香港政府2024年的财政赤字可以观察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完成了它的战略目标,香港转口贸易的市场份额在2019暴动和新冠疫情的打击下持续缩减,暴动群体亲手将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文化影响力变得遗臭万年,外资逐年撤离以及减少,使香港政府面临巨大财政压力,在2024-2025年两年间持续克扣社会福利,大力鼓吹旅游业发展,放开了所有投资门槛,并且试图通过营销各种节目以挽回这座城市的声誉。只要香港的经济活动萎缩——离岸人民币的可操作性就会下降,这样美帝国主义者就达到了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然,港区《国安法》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不止于此,经历了一场动荡,香港当局已经患上了创伤应激综合症,《国安法》的运用变得非常广泛,任何对于中国的批评也已经开始慢慢受到管制,这一点在教育机构展现的尤为明显:香港政府以及香港教育局在2021年后制定了新的一套教育程序,将国安教育纳入教育体系里。不过,手法非常生疏拙劣,基本不涉及对中国历史的着重教育,也不牵涉任何革命历史的宣传,有的只是对现代成就的重复鼓吹,因此在基层反响基本不大,而且形式上的强迫突然杀进了香港人一贯的生活模式,使那些掩盖在笑脸下的不满更为极端不适。在教育系统外,自2019年起已再无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集会,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集会都容易被打上“违反国安法”的罪名——这显然断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活路,本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下要组织起无产阶级已经是难如登天,现如今集会和言论也将受到管制,这使得要在香港组织起社会主义革命变得遥遥无期,这也告诉了我们同志,单纯反抗共同的敌人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一场幼稚、狗咬狗的政治暴动,很可能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