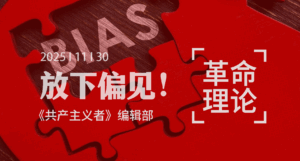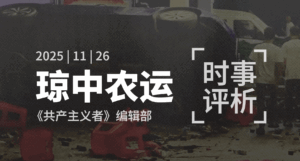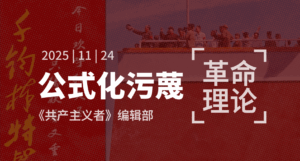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本文是一篇对于文艺和文化性质的短评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们的形态和发展在某种程度内决定于社会的物质基础,它们与这个基础相适应,并且反映了建筑于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和时代。文化和艺术的表现形式本身具有类似生产资料的工具性,但是使用它的创作者和艺术家们通过艺术呈现的方式传播自身的主体性,因而艺术作品反映出艺术表达形式本身所不具有的阶级倾向性,但是这一阶级倾向性通过艺术的表达方法间接地体现,其起到的作用是通过艺术家之手呈现现实社会,而非直接呈现艺术家本人的全部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就指出过:“大家知道,在艺术上,它的某些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同那成为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也决不是成比例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写道:“……我们要告诉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在那些涉及思想发展的问题中,就算是非常熟悉‘弦’(注释:此地指生产力的发展)的人,如果他们不赋有某种特殊才能,即艺术感觉,也可能无法去解释历史过程的。心理自行适应于经济。但这个适应乃是一种复杂过程,为的要了解其全部进程,且能生动地给自己与别人描绘出来,描绘得有如真实发生一般,那末不止一次地需要有艺术家的才能。”文艺是情感的多于理智的;幻想的多于纪实的;潜意识的多于有意识的;浑统体会的多于分析理解的;形象的多于理论的;表现的多于议论的。一切文艺都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的一部分。
恩格斯对于巴尔札克和歌德所说的话,点出阶级性和艺术的阶级倾向性不是一个东西。恩格斯一方面说巴尔札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另一方面却说他“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佐拉都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为什么一个思想上十分反动的人,却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来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因为这个艺术家采取了正确的艺术创作方法的原因。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巴尔扎克所处的1815-1848年法国社会转型期(这个时候的社会情况是:封建贵族特权加速瓦解、资产阶级全面掌权、小生产者工人化)为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空前丰富的矛盾素材。恩格斯说,“我所提到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一个作家采取什么创作方法,问题主要不在于他有意识的选择,而更在于他整个艺术修养与艺术才能所决定的方法。因此,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意思,显然不是仅要推荐一个好的创作道路,而且还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不是由他的思想观点来决定,而是由艺术家的创作才能来决定的。无论作者本人倾向如何,他想给作品灌输什么样的阶级倾向,文艺都是可以独立于作者本人的倾向并表达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内容的。例如在《老姑娘》中,巴尔扎克塑造了科尔蒙小姐这一旧贵族女性形象。作者试图通过她坚守封建婚姻观、拒绝资产阶级新贵的“正派”姿态,批判复辟时期贵族价值观的迂腐。然而,科尔蒙对求婚者滑稽的挑剔(如因对方“纽扣太亮”而否决)、对家族纹章病态的执念,使其沦为笑柄。这种讽刺效果恰恰源于巴尔扎克对细节的现实主义描摹,当科尔蒙庄严宣布“宁可独身也要维护血统纯洁”时,读者看见的却是被时代抛弃者的滑稽表演。作者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撕裂,恰恰暴露了旧道德在资本逻辑碾压下的荒诞本质。
另外,艺术形式由艺术内容产生,与内容同一。虽然内容占首位,但形式可以反作用于内容,它从不居于被动地位。这种关系是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非常相似的。在中国艺术发展脉络中,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呈现鲜明轨迹: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起印证了形式对内容的能动性,例如《金瓶梅》突破章回体传统框架,以市井白描手法承载商品经济萌芽期的世情百态,其嵌套式叙事结构恰与晚明社会阶层流动的复杂性形成同构。至清中叶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更以“草蛇灰线”的网状叙事呼应旧式家族解体的历史必然,诗词判词等传统文学形式也被创造性转化为人物命运的预言系统。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尝试集》打破格律束缚的白话诗实验,实为启蒙思想传播的必然要求,自由体形式使“德先生”“赛先生”等新观念获得通俗化表达渠道。这种形式创新随后在1940年代延安文艺中发展为“民族形式、革命内容”的创作原则,例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采用评书体小说形式,使婚姻自主的新思想通过农民熟悉的艺术载体广泛传播。
关于文艺的生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说:“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商发财,也就是说,他为薪金而生产劳动。”此外,马克思还写到过“列如弥尔顿创作的诗乐园得到了5磅,它是非生产劳动,相反,书商提供工厂是劳动的作家,只是生产劳动者,米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的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磅,但是在书商支持下编写书籍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它的产品从一开始就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但是同一个这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她生产资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第432页)艺术被社会承认后,就必然带有经济基础的属性了。雕塑、绘画、音乐、建筑、工艺,都是生产的产物,甚至能像食品布匹一样,在价值规律和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进行消费流通,艺术生产者将自己的审美体验物化为艺术产品的过程,这必然涉及包括艺术技巧在内的艺术生产力的各种元素。
当弥尔顿创作《失乐园》时,“就像春蚕吐丝般遵循其天性”,这种非雇佣劳动属于“自由的精神生产”范畴;而当莱比锡的无产者作家受书商雇佣进行写作时,其创作活动就转变为“为资本增殖服务的生产劳动”。这种区分并非否定艺术创作的精神价值,而是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艺术生产必然分裂为两个向度——它既是审美体验的物化过程,又是价值规律支配下的商品生产。艺术产品的这种二重性,在文化工业化进程中呈现为愈发尖锐的矛盾:雕塑、绘画等传统艺术形式原本承载着人类审美能力的对象化,但当它们被纳入市场交换体系后,其使用价值(审美功能)就不得不屈从于交换价值(利润追求)。即便是最富创造性的艺术技巧,也会在资本逻辑的规训下转化为“艺术生产力”的组成要素。
传统文艺生产的物质性变现依赖实体载体,例如雕塑家消耗大理石,画家使用颜料画布,作家依托纸张油墨完成价值转换。而现代互联网文艺生产则重构了这种物质基础:短视频平台创作者通过算法推荐机制将注意力转化为广告分成,YouTube博主依靠流量数据获取品牌赞助,网络小说平台将文字转化为数字货币打赏与付费订阅。这种转变并未消解马克思揭示的基本矛盾,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强化了资本对艺术生产的控制:动漫产业的IP开发要求角色设定必须适配周边商品化;短视频的“黄金三秒”法则迫使创作者将艺术表达压缩为可量化的数据指标;网络文学平台通过AI监测用户阅读行为数据,以算法推荐机制引导创作方向维持付费率。数字技术的非物质表象下,实则是服务器算力、光纤网络与用户行为数据的物质性支撑,艺术生产力在此过程中被彻底整合进全球数据资本主义的价值链。
然而,真正的艺术创造始终包含着突破这种异化的潜能。例如弥尔顿的《失乐园》虽被标价三先令出售,其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却超越了具体交易行为的历史局限性。此外,现代日本二次元文化中的《寄生兽》通过物种竞争寓言反思环境危机,《心理测量者》也借反乌托邦设定剖析技术统治的异化。这些案例表明,当创作者具备足够洞察力时,即便在商业化框架下,作品仍能自发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甚至违背创作者初衷——正如《魔法少女小圆》解构了传统魔法少女作品叙事,最终展现个人面对系统性暴力的不可抗性,远超单纯娱乐文本的边界。
此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后,非革命文艺会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对此负有责任的完全不是造纸工业管理总局。因为,即使当时缺乏纸张印诗,现在总可以印了。不一定要赞成革命的诗,哪怕有些反对革命的诗也好。国外的文学我们是清楚的:完全是一个零……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进入了俄国人民的命运,对一切事物表明自己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断。过去立即离去了,暗淡了,枯萎了,只有站在十月革命立场上的回顾才能艺术地复活过去。谁置身在十月革命的前景之外,谁就会完全地和永远地变得精神空虚。因此,那些对此‘不赞成’或与此‘不沾边’的智者和诗人都成了精神空虚者。他们实在也无话可说。正是因为这一点而非其他原因,流亡文学是不存在的。对不存在的东西就无法评断。”(《文学与革命》)
以下是一些具体例子:殷海光在1949年后,在台创办《自由中国》杂志,撰写批判中共的“威权政体”的文章。1960年杂志遭查封后,其著作被禁,流亡海外期间所撰文章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汉学家评为“脱离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逻辑演绎”;王晓波在1970年代地下写作的《沉默的大多数》等作品在1990年代公开出版后,从未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学界重视过,因而也罕有相关的学术引用记录。
1959年革命后,流亡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移居伦敦,创作实验小说《三只悲伤的老虎》(1967)。尽管获西班牙简明丛书奖,但拉美文学界批评其脱离古巴现实,沉迷语言游戏。墨西哥评论家卡洛斯·蒙西瓦伊斯称其“技术华丽却无古巴之魂”,作品在拉美影响有限。
1960年代,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以神秘主义小说《哈扎尔辞典》(1984)闻名,但早期流亡时期作品如《铁幕后的风》(1959)因政治化叙事,而在尝试出版时遭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版商拒绝。德国文学杂志《墨丘利》指出其“反共口号替代了艺术真实”,未获严肃关注。
1975年独立后,诗人路易斯·帕特里西奥·德索萨流亡葡萄牙,出版诗集《流亡者的地图》(1977)。莫桑比克文学学者安娜·玛法尔达称其“沉溺于个人苦闷”,缺乏对本土解放运动的观察。该书在葡萄牙语世界销量不足500册。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把革命文艺等同于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纯粹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因为这种“文艺”恰恰是会毁灭文艺的。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曾强调“艺术的最第一的条件,是向著艺术的内底要求,是真实”(第74页),并指出勃洛克的诗作《十二个》之所以伟大,恰在于其未被“革命标语”束缚,而是“从艺术的本体出来的诗”(第75页)。托洛茨基还批判道,如果将文学视为“阶级的留声机”,认为“无产阶级在过渡期对艺术的政策,只能是帮助艺术去理解历史意欲的宏伟”。(第83页)托洛茨基还指斥未来派“将艺术降格为政治的插图”(第79页)。而鲁迅在《十二个·后记》、《文学的阶级性》、《三闲集》中呼应了此观点,认为革命文学若仅“打打打”“杀杀杀”,便沦为“空洞的噪音”。鲁迅还称“口号教条”只会制造“符咒”而非文学。鲁迅在《〈艺术论〉译本序》中又进一步批判“硬填口号”的作品“往往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二心集》)。
可见,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鲁迅,都强调文学应直面生存困境,揭露精神奴役的创伤,而非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当创作者将复杂的社会关系压缩为政治标语,用概念化的人物图解理论教条,这种“遵命文学”便丧失了艺术真实的生命力。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指斥“瞒和骗”的文艺消解了批判精神,使文学沦为粉饰现实的油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常以群体代言自居,却漠视个体灵魂的震颤,用抽象理念覆盖具体生命的痛感。真正的革命文艺(真正的革命文艺可能会有现实主义文艺,但它本身不等于现实主义文艺)的创作立场拒绝任何先验的“主义”绑架。
高于艺术和文学的东西是我们所称为文化的建构本身。在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文化并未作为独立的精神生产领域存在。即便在奴隶制社会初期,也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可供统治阶级通过物质优势独占、并能作为商品输出的文化形态。此时的审美意识直接根植于物质生产实践,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那样:“劳动产品的实用性与形式美的统一,构成了原始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与物质生产直接同一的文化形态,反映着原始公有制的社会关系。
随着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深化,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逐步确立。在邦统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古代帝国和欧洲封建社会中,祭司阶层与世俗统治者共同垄断了文化解释权。无论是古罗马的元老院文学还是中国秦汉的经学体系,这些被神圣化的文化形态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的:“不过是阶级统治的思想外衣,用普遍性话语掩盖特殊利益。”这种文化垄断在资本主义时代达到新高度。资产阶级在破除封建文化桎梏的同时,又将文化纳入商品生产体系,使其成为资本增值的特殊载体。
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化大生产彻底改变了文化存在样态。手工业时代潜藏在工匠技艺中的传统美学,在标准化流水线前逐渐消逝。这种文化异化现象印证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断:“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资产阶级在摧毁传统工艺的同时,又通过博物馆制度和复古主义思潮制造出文化补偿机制,将前工业时代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巩固阶级统治的符号资本。到了20世纪,从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到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工程,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制度修补维持文化霸权,却始终无法解决文化生产社会化与占有私人化之间的根本冲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建构,必须建立在消灭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当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强制性分工消失之时,文化将不再是特定阶级的专属领域或商品化符号。这种文化解放不是简单否定传统,而是如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强调的那样:“吸收人类全部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未来的“文化”概念终将扬弃其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形态,复归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规定:文化将会成为全体劳动者共同创造、自由享有的精神财富,最终服务于人的创造力解放与综合素质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