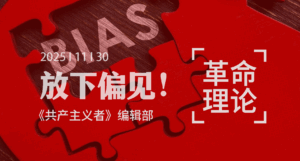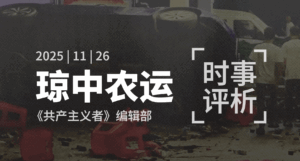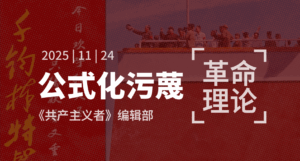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资产阶级的统治绝非是单纯通过暴力的手段维持的,更不只存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层面。为了创造一个适合资本主义平稳运行的环境而不是处在崩溃边缘的战场,资本主义越来越依靠与通过意识形态与精神文化等手段塑造出一种思想上的“霸权”,以充满偏见的“常识”正当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与不公,磨灭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
家庭、媒体、宗教场所、工会、文化机构(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学术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学校等)、政党、专业协会(如律师协会、医生协会等)、社区组织(邻里协会、地方团体等)、公共集会、法律机构(民间调解部分)这些非国家机构的社会机构都是构成精神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其精神生产的内容最终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另外,精神生产资料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关系本身,而非国家结构,而且其运作本质上也是生产关系的反映,而非独立自主的结构。而且,人也并非只是意识形态的被动执行者,随着客观物质环境的变动,原本作为“被动的臣民”的主体也可能会变得“桀骜不驯”,从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精神生产资料的掌控与争夺始终呈现动态博弈的特征。这种动态性体现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对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反复拉锯中。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们(也就是反映在文化上的统治阶级)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来巩固整个阶级的文化霸权,但被统治群体则可能利用同一套机制进行抵抗或重构。这种争夺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多重主体参与的复杂博弈。
以14世纪佛罗伦萨梳毛工人起义(1378年)为例,当时的行会组织(如羊毛业行会,另外,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城市行会不仅是经济组织,还承担着民兵训练、慈善救济和戏剧表演功能)长期被大商人垄断,排斥底层工人。梳毛工通过街头集会、占领市政厅并要求组建独立行会,迫使当局短暂承认其政治权利。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行会制度首次被底层群体改造为阶级抗争的工具。这种对精神生产资料的创造性运用,使得原本维护封建行会制度的机构转变为阶级斗争的战场之一。
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工具,精神生产资料通过日常化的运作将生产关系自然化。在古罗马奴隶制社会中,家庭祭祀活动、角斗士表演和广场辩论共同构成了维护奴隶主权威的意识形态网络。家长通过家庭祭祀仪式强化父权权威,角斗场表演将暴力统治美学化,广场辩论则将公民权严格限定在自由民阶层。这些实践将奴隶制的剥削关系转化为“自然秩序”,使奴隶群体将自身处境理解为神意安排。但公元前1世纪的斯巴达克斯起义表明,角斗士训练营这个原本用于规训奴隶的场所,反而成为起义者军事训练和组织动员的基地,说明再生产工具本身包含着被颠覆的可能。
在古代中国的秦汉时期,乡约组织通过道德评议、互助借贷和婚丧仪典,将法家秩序和儒家伦理渗透到基层社会。唐代敦煌文书显示,当地社邑组织不仅管理佛事活动,还承担水利分配、纠纷调解等职能,形成独立于官府的地方自治体系。明代的东林书院网络通过讲学活动传播政治理念,其成员利用科举同年关系构建跨地域联盟,最终发展成对抗宦官集团的士大夫集团。这些案例证明,即便在中央集权体制下,非官方的精神生产资料仍保持着相对自主的运作空间。
此外,在日本江户时代,其村落共同体通过“讲”组织(如富士讲、伊势讲)进行宗教活动,这些团体逐渐演变为农产品流通网络和信贷机构。当19世纪幕府推行货币地租改革时,关东农民也通过借富士讲网络串联,发起反对货币地租的集体请愿(如甲斐国农民一揆),最终迫使幕府暂缓征税改革,迫使当局调整税收政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资料则呈现出全球化特征,但并未改变其压迫和剥削的本质。跨国科技公司的开放源代码运动看似打破知识垄断,实则通过众包模式将开发者纳入资本积累体系;印度班加罗尔的IT培训机构表面传授技术知识,实质是为全球价值链培养廉价劳动力;中国电商平台的用户评价系统本应反映消费者意见,却演变为商家刷单控评的战场。这些新形态的精神生产资料控制手段,依然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需求。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精神生产资料争夺开辟了新场域。社交媒体算法推荐机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新焦点,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性被同时用于金融投机和社会实验,在线教育平台的知识传播日益卷入文化领导权争夺。2020年美国“黑命贵”运动中,抗议者通过TikTok短视频突破传统媒体封锁,组织全球声援网络,这种技术赋能的社会动员重新定义了精神生产资料的范围。
历史经验表明,精神生产资料的争夺存在周期性规律。当物质生产领域发生重大变革时,其配套的精神生产资料的控制效能会逐渐减弱。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期间,工人阶级以《北极星报》为喉舌,依托宪章派教堂和互助合作社,构建起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会组织利用广播节目和工人戏剧,成功短暂地突破了资本家对传统媒体的垄断。这些斗争都发生在旧生产关系难以维系的历史节点,印证了精神生产资料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层关联。
可见,精神生产资料的演变轨迹始终与生产方式保持辩证关系。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推动宗教改革,但其物质基础是地中海贸易网络重组带来的城市经济勃兴。这提醒我们,精神生产资料的动态博弈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来理解,其变革既是社会转型的表征,也是推动转型的重要力量。
“自由意志”的幻觉
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和劳动的工人们客观上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作用,因此他们在客观上一直在反革命,这是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工人们可以选择服从,也可以选择死亡表示反抗,因为人总是有选择,不存在‘被逼的’,因为人不是动物,人可以战胜生物本能”。这里我们将反驳这两个命题,以进一步正确认识意识形态。
第一个命题的错误在于混淆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客观强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明确指出:“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工人为生存被迫出卖劳动力,这种结构性暴力使他们的劳动客观上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绝不构成什么“反革命行为”,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统治阶级通过“市民社会”(即精神生产资料)建立文化霸权,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化”为“永恒秩序”。工人对生存需求的服从,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制造的“常识”,而非主观政治选择。
第二个命题的荒谬性首先暴露于其逻辑悖论:若“人不是动物”意味着必须否定生物本能,则“选择生存”反而成了动物性行为,而“选择死亡”才是“人”的证明。然而,这种二元对立甚至在纯粹形式逻辑层面也已自相矛盾。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可见,自由意志也需要以生命存续为前提,以死亡为代价的“反抗”恰恰取消了自由意志的物质载体,那这算什么“自由”呢?当资本主义将基本生存条件异化为必须通过雇佣劳动换取的商品时,“服从或死亡”的“选择”实质是暴力下的形式自由。因此,葛兰西揭示的“无人相信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却仍在正常运行”的意识形态机制在此凸显:工人明知剥削存在,并嘲笑所谓“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鸡汤,但仍将工厂制度视为“自然的空气”,这种“实践意识的矛盾”恰恰证伪了抽象的“自由意志”的存在。资本主义通过教育、法律等机构将“服从”建构为“道德义务”,使工人即便识破意识形态谎言,仍不得不“假装相信”。这种结构性暴力远非个人意志所能对抗。当你只是为了吃饭,而在一天内做两份甚至三份工作,每天进行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你还能谈论什么“人可以战胜生物本能”么?因此,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采取集体的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批判”打碎资本主义。
顺从不自觉的习得
首先我们要明白,生产关系在个体实践层面表现为“政治权力”的分配,即人们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直接决定了其可行使或被迫服从的权威关系。这种权力不仅体现在宏观制度中,更通过日常互动、行为规范与身份认同渗透到个体生存的细节,使经济角色与政治支配密不可分。这种渗透往往通过精神生产资料的运作实现——学校、宗族祠堂、行会组织等机构以知识传授、道德训诫、技艺传承为载体,将统治阶层的价值观转化为被广泛接受的“常识”。
以封建社会为例,农奴依附于领主土地,其耕种、婚配甚至迁徙均需获得领主许可。劳役地租的缴纳不仅是经济义务,更是对领主司法权、军事权的承认。农奴在田间弯腰收割的动作本身,便是对“人身依附”这一政治权力结构的身体化实践。中世纪欧洲修道院推行的“七艺”教育体系,通过语法、逻辑、修辞等课程塑造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使他们对“上帝—教会—领主”的等级秩序产生理性认同。这种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让农奴将普遍文盲的状态视为“上帝安排的智慧分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表面拥有“自由”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但流水线上的计时器、绩效指标与监控系统将资本家的支配权具象化为分钟级的劳动控制。工人对加班与否的“自愿选择”,实则是失业恐惧与生存压力构成的隐形强制,其每一次服从生产节奏的举动都在微观层面再生产着资本的政治权威。现代企业推行的“企业文化培训”也构成了精神生产资料,现代企业通过“奋斗者协议”“使命宣言”等话语体系(如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中“Ownership”条款),将资本增值逻辑包装为个人奋斗叙事,使工人将超额劳动误解为自我实现的途径。
在邦统制生产方式下,中央集权通过水利工程等公共劳动组织,将农民纳入官僚系统的直接管理。个体参与挖渠筑坝时,不仅贡献劳动力,更通过集体协作强化对专制君权的认同。疏浚河道的行为既是经济生产,也是向皇权缴付“政治忠诚”的仪式。清代保甲制要求每户悬挂门牌登记家庭成员,并依托乡约宣讲将户籍管控与“忠孝”伦理结合,使农民在日常出入家门时都重复确认自身在精神生产资料体系中的位置。秦代“以吏为师”政策更直接让基层官吏兼任法律讲解员和道德教师,在陕西云梦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中,明确要求官吏既要精通律令又要传播“忠孝”观念。
这些例子表明,生产关系绝非抽象的经济关系,它总是通过具体的权力操作将人固定在等级秩序中:谁决定劳动内容、谁掌控劳动成果、谁制定劳动规则。(当然,微观权力关系始终锚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核心,因为它是作为作为再生产工具出现的)精神生产资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知识分类(如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范围)、记忆塑造(如企业年会的“司歌合唱”)、空间规训(如互联网公司的开放式办公布局)等方式,将支配关系植入个体的认知结构和情感反应。19世纪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不仅维持治安,还通过出版《点石斋画报》将巡捕暴力美化为“秩序维护”,这种视觉化叙事比法律条文更能潜移默化地重构人们对权力的认知。像是现代算法推荐系统看似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实则依据用户数据画像进行意识形态定向投送。算法推荐系统依据用户画像差异化灌输意识形态(如劳工群体高频接收“宿命论”内容,精英群体更多获取“风险控制”叙事),使得阶级认知区隔得以再生产。这种精神生产资料的差异化供给,在微观层面持续巩固着阶级认知的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