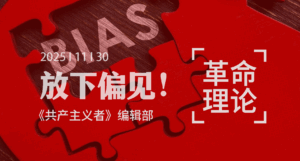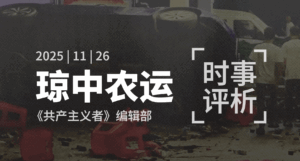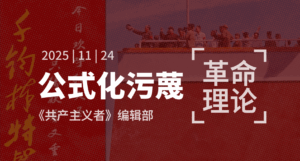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科学”思维
在21世纪,算法推送的茧房效应和社交媒体上的谣言风暴时刻都在提醒我们:科技越发达,越需要科学的思维穿透表象来分析问题。科学的精神是革命者有效、正确处理信息的必备工具:它教会我们用证据替代偏见,以逻辑对抗情绪,并保持清醒的判断力。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和其他社会思想与政治理论不同的核心在于其“科学性”——它不是武断或臆想。但它自己宣布自己是科学并不代表它就是科学了,其研究方法必须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被称之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认识,终归是在从“政治表面”向“社会生活的深度”了解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必须发现潜藏在“按照经济科学”的社会生活的底部的“某些事物”。“现代历史著述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所谓科学,就是意味着发掘出隐藏于此类现象背后的本质:“前者(‘一切表现形式’,即现象)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而后者(‘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即本质)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再比如在资本论中谈到“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时,马克思已经将现实世界中现象与本质的分离一语道破。“既然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它是用何种方式进行的呢?答案是抽象力,也就是说运用抽象力而实现的抽象这一活动。
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闻名的记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抽象所面,对的对象就是现实。而被抽象的现实则表现为“范畴”。所以,具有科学性的作品,即使看似是在罗列“范畴”,其实也是将被抽象的现实进行观念再建造的结果。在表面观察中无法捕捉到的本质现实,以科学的手段被再建造,从而得以表现出来。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蒲鲁东,也是由于这点。“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此外,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所谓科学,无非便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程序,不断探求事物的“为什么”和“为了什么”的工作。
这里我们要明确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后者将科学简化为对孤立事实的观察、实验与归纳,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批判的“小买卖”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将自然现象切割为碎片化的局部,用机械的因果关系解释整体世界。那种科学,就是所谓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恰恰体现在对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把握,这种思维在21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
现代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宏观系统论与微观机制论的辩证统一。在宏观层面,生态学揭示了生物圈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的整体性规律,气候模型展现地球系统的非线性反馈机制,这些复杂系统的理论体系证明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层展”现象。这些发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与运动转化的基本原理。而微观层面的分子生物学、纳米技术等则通过精密实验揭示物质结构的深层机制。解剖刀下看到的不是器官,而是组织的形成过程。两种研究路径看似对立,实则构成科学认知的完整图景:宏观规律为微观研究提供方向指引,微观机制为宏观现象提供物质基础,这正是辩证思维中“对立统一”原则的体现。
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层展论”为这种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注解。当生态学家研究森林碳汇功能时,既需要理解树木光合作用的分子机制,更要把握气候、土壤、生物群落构成的系统网络;当经济学家分析全球产业链时,既要考察具体企业的生产成本,更需揭示资本积累与空间重构的历史规律。自然科学在微观实证中积累的知识碎片,需要通过辩证思维整合为对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整体把握,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超越传统实证主义的关键。可见,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替代具体科学研究的“科学之科学”,也不是与实证方法对立的玄学思辨,而是为处理复杂系统问题提供了宏观的方法论指南的科学。
所谓“真理”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把自己视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正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实践哲学是以过去的一切文化为前提的。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了作为对它的批判的实践哲学。黑格尔的内在论变成历史主义,但只有在实践哲学那里,它才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的历史主义或绝对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本身也必将在文化的发展中被取代,这种取代将意味着人类意识已取得一致,并且这种一致是以一种把必然性完全吸收到自由之中的社会形式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并未否认过自身必然会被否定,同时还指出自身在未来必然被否定。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前,是不可能被真正否定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有一段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法国物理学家雷诺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会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对它作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它的表述方式。可见,关于最后的“终极真理”,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式的道德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碰到,它们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做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可见,人类的认识就其本性而言,对于漫长的历史发展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但是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科学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认识,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个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无条件的真理权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前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可见,人的思维既是至上的,又是不至上的。思维的至上性体现在其本性和终极目的上,但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由于个体和历史的局限性,思维又是不至上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可以把“现象界”和“物自体”相连接。
道德、“人性”
为了防止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本质主义”,因此在这里顺便提一嘴马克思主义对“本质”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的“本质”始终是实践的、动态的,它强调本质的社会建构性和历史条件性,将本质视为一定历史的产物。
对于本质主义(尤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观)试图通过抽象概念(如“人性”“事物的永恒本质”)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些理论忽视了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本质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而非先验的、固定的。本质主义常将事物的本质归结为某种普遍性(如柏拉图的“理念”、宗教的“灵魂”),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普遍性是意识形态的,掩盖了具体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关系。
此外,马克思的写作方式突破了本质主义对固定范畴的静态考察,转而通过辩证法的动态逻辑揭示现实关系。他拒绝用“XX是什么”的抽象定义框定社会现象,而是以历史具体性为基点,展现事物内部矛盾推动的演进过程。以商品分析为例,他并未给出本质主义的固化定义,而是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切入,呈现商品形态如何经由市场交换向货币转化,最终形成资本增殖的矛盾运动。这种正题(商品二重性)-反题(价值形式异化)-合题(资本逻辑生成)的螺旋式推演,使概念在自我扬弃中获得新的历史规定性。(本文也会使用这种写作方法写作)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将商品本质视为永恒自然属性的谬误,指出商品本质实则是特定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呈现——劳动异化使得价值成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辩证思维在文本中表现为表面”混乱”的逻辑展开,本质上正是对社会关系动态性的理论映照。马克思主义通过这种辩证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具有历史动态性,例如阶级属性随着生产方式变革而演化(如封建领主向资本家的转变),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的,自然与社会规律都具有历史性,本质是“过程的集合体”。
马克思主义也特别强调实践的基础性作用,认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是理解本质的关键场域。事物的本质并非独立于实践的先验存在,而是在实践中被不断重构。以劳动为例,它不仅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物质过程,更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赋予产品交换价值的属性。当劳动产品脱离具体社会环境时,其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便随之消解。这印证了交换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形态,而非物品的固有属性。
马克思主义既然重视“科学方法”,那么它会怎么看待道德呢?(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科学分析必须和道德“结合”,才更能接近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道德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并且跟一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利益相联系的,不存在永恒的合适任何人的道德真理。因此,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道德说教,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科学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组织行动时坚持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一个手段只能由它的目的来使其正当,但目的本身必须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例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虽然客观上带来了铁路和电报系统,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殖民统治和资本积累,手段上的“文明开化”无法改变整体非正义性。目的和手段不是相互割裂的,目的本身就排除了一部分手段——正如我们不能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手段实现和平,也无法通过雇佣劳动制建成共产主义。
实现正当目的的手段都可视作正当,但这些手段必须与目的保持本质同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例如苏联对芬兰的冬季战争反映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扭曲,其手段违背了国际主义原则,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也存在程序瑕疵,但这些行动在最终都终结了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对工农的压迫,从整体来看,这些行为实际上是进步的,是“道德的”。
康德的“绝对命令”主张道德法则应具备普遍性与无条件性,但单单是中国的历史表明,道德标准与“善良”“邪恶”的界定始终随社会结构、政治需求与文化思潮变动,难以形成超越时空的绝对准则。商周时期,周人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取代商朝神权政治,将“德”定义为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政治品格,此时“德”与政权合法性绑定,具有鲜明的功利性。至春秋战国,儒家将“仁”塑造为内在道德核心,而法家则宣称“法”高于“义”,商鞅以严刑峻法重构秦国的善恶标准,证明同一时代不同学派对道德的理解已存在根本冲突。汉代“独尊儒术”表面确立伦理统一性,但统治实践中“外儒内法”的策略,使得道德教条常为现实政治妥协,如汉武帝以“盐铁官营”压制商人,将经济竞争行为污名化为“与民争利”,实则服务于统治需求。
此外,宋明理学试图以“天理”统摄道德,将“三纲五常”绝对化,但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催生士商阶层融合,传统“重义轻利”观念逐渐松动,徽商等群体通过“贾而好儒”重塑商业伦理,证明经济基础变动必然冲击道德教条。近代以来,道德标准的颠覆更为剧烈:新文化运动批判“礼教吃人”,将传统家庭伦理视为封建压迫;社会主义革命又用阶级斗争的标准重新定义了善恶,例如地主阶级的慈善行为被重构为“剥削伪装”,到了20世纪60年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又成为了最高道德律令,青年在“破四旧”中摧毁宗庙祠堂,将孝道斥为“封建糟粕”,而子女揭发父母“罪行”也会被视为“大义灭亲”而合理化。
历史证明,道德从来不是先验的绝对法则,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权力、利益与文化博弈的产物。从周人的“德治”到中国工人国家的“革命美德”,中国社会对善恶的评判始终服务于现实秩序的重建,康德的“绝对命令”无法解释这种道德相对性与历史流动性。当道德标准随时代更迭不断被解构与重构时,所谓“普遍必然”的伦理原则不过是形而上的幻象。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道德的批判并非完全否定道德本身的能起到的一定的作用,而是揭示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历史暂时性。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用了不少“道德谴责”。这是为什么?
道德话语的运用在马克思理论中具有三重逻辑基础。首先,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并非基于先验价值预设,而是从科学分析中推导出的客观结论。例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证明的剥削机制,在工人意识层面必然表现为“不公正”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的理性化过程就是阶级意识的形成路径。
其次,“道德批判”在这里也可以作为意识转化的催化剂,在认识论层面架起了科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的逻辑桥梁。工人对“剥削”的道德愤怒,实为对劳动力商品化本质的感性把握,这种情感能量推动其跨越“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认识鸿沟。最后,这种“道德谴责”的历史特殊性使其能够让工人阶级在主观上突破意识形态。当资产阶级用“自由”“平等”粉饰雇佣劳动制时,马克思通过揭示契约自由背后的强制劳动本质,使“道德批判”成为撕破意识形态伪装的解剖刀之一。
这种辩证运用之所以可能,根源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主客体关系的重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矛盾必然在主体意识中投射为道德异化感,科学理论的任务不是否认这种主观体验,而是将其提升为对历史规律的自觉认知。当工人意识到流水线上的压迫不仅是个人遭遇,更是系统性的价值剥夺时,“道德批判”就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阶级立场”“道德批判”必须是科学分析的结果,这两者必须服从科学,而不是让科学服从立场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