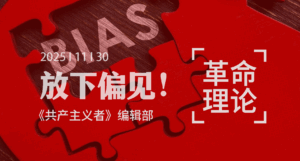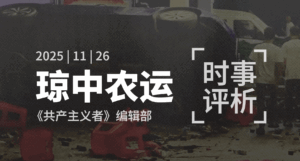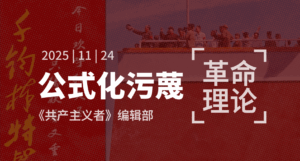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他们孜孜不倦地在中国重建着资本主义秩序,开动国家机器宣扬其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再生产符合资产阶级需求的劳动力,并按需塑造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迷失自我,误认自我,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
学校在中国拥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崇高性与权威性,以至于资产阶级不断悄悄在学校灌输给工农大众子女的教育的内容上做文章,从而不仅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思想与精神上不断加固着缠绕在中国无产阶级身上的铁链,妄图从根本上消除人民群众重新当家做主的机会。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血泪、愚昧与无奈的当代教育体制进行彻底而无情的揭露。
异化教育
除了北京、上海、新疆这些臭名昭……赫赫有名的省份或自治区以外,大多数的地方的高中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是不需多说而一目了然的。结束了义务教育进入高中的高中生们,首先充当起合格的家庭投资的对象,承载着人民群众试图再生产家庭自身维持存续的期盼,其次作为即将投入劳动力生产厂的原料,走上了传送带。为了在如今生存环境越来越险峻的社会上生活下去,难免增大了学生间的竞争,学生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往往甚至大于了学生与老师间的对立。尤其是在实验班这类地方,在学校对假期尤其是实验班的假期的疯狂克扣尚不明显的日子里,众多优等生自动建构起的学生之间的规训,虽然确实对各种影响他人的恶劣行径起到了相当的抑制作用,然而其又难免会在其他方面加剧对于学生个性的抑制。
等等,什么?学校会抑制学生的个性?我们在北京四中参加舞会的亲爱的同学们可不这么想。
然而,对于学生个性的抑制,竞争所导致的学生间的对立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不难了解到现代教育制度,事实上缘起于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工厂制度。作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运而生以满足生产组织需要的现代工厂制度马不停蹄地催生了现代教育制度,后者自然地是以青年提前适应工厂生活为目的的同时,进行最基础的通识教育,使之满足工业革命发展的基本需求。
“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资本主义社会下,一切都是为了资本的积累也即劳动的积累而服务的。学校作为一个脱产的机构,却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社会。学校为社会生产资产阶级需要的温顺的雇佣奴隶,那么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学生当然只能作为原材料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优等生与差等生的区别如此之大,甚至出现了实验班这种专门向优等生,也即最符合资产阶级需求,最能卖个好价钱的学生群体倾斜大量教学资源的地方。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实验班的同学,是“优等的材料”,在“加工”后,更能为学校乃至资产阶级带来利润罢了。而对于学校来说,特别是对于城市中的什么贵族学校重点高中与乡镇中学的区分来说,也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为不同的阶级倾斜不同的资源,从而保持甚至加剧阶级的分化,加剧劳动者的分化。总归还是操纵起奇妙的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手,维护起自己的宝座。
在将学校抽象为一个加工学生这种原材料的工厂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学生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由人“升级”成为了什么——人变成了物。物化,异化,外化。
“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
成绩,这个本应只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程度的表现的东西,摇身一变成为了学生学习活动的最终结果——学习成果的表现变为了学习成果本身。成绩实实在在地表现为结果,成绩实实在在地对象化、现实化了,然而进行学习活动的学生,却可悲地非现实化了。工人非现实化为饿死,学生非现实化为跳楼。 成绩宛如成为了学习唯一的最终目的,而过程、方式,与学生首先作为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则宛如明月旁的繁星般黯淡了。我们学到的果真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我们的成绩果真能够并且应当代表我们全部的学习成果吗?所用来标签化我们每个人的成绩的,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体异化劳动的性质和我国特殊的机械化的教育体制所导致的在校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果与个人需求所脱离而已。
“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这完全是撒谎,……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
当今高中生在学习过程中,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是在真正快乐主动地在学习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学习为我们带来快乐的时候——学会某一个技能的时候,理解某一个思想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成就感,满足感,眼界豁然又开朗了一些,禁不住为自己的进步而高兴。然而学校,乃至现代教育制度对于学习成果的标准化,将会无情地抹杀大部分这种快乐——比如我学到了一个技能,可是这个技能高考不考;又比如我理解了某一个哲学思想,可是高考又不考哲学。同学们在发展兴趣爱好的时候,我猜大家或多或少都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你学的这个高考又不考,学这个干嘛用”或“现在好好学习等大学再学吧”。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
真正的学习过程应当是主动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理科知识标准化是必须的,然而相当一部分知识,例如语文,历史,政治等方面的知识的掌握或许更应当是独立的而非庸俗的一个过程。等等,为什么学校连文科的一些知识思想的学习也要标准化呢?我们不得不认识国家的本质即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认识到,这样的文科标准答案的限制是由于学校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份子而产生的。学校是国家宣传本身统治合法性与正统性的重要场所。然而现代教育制度对于学习过程与学习内容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与附着在其上的填鸭式教学,应试教育,所有这些构成的这种虚假的学习所带给学生的只能是痛苦、焦虑、抑郁,甚至是自杀,正如劳动的异化所带给工人的东西一样。
工厂和教室
对工人,资产阶级将劳动产品与劳动者进行了异化:劳动者在生产线上往往只能生产产品或者服务的一部分,从产品或者服务中再也看不出是哪个人生产的,资本家从生产线中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将其粉饰为经营的利润。生产过程中工人变成了机器,只是单调重复着无意义的动作。劳动不再是自由的、创造性的,而是强制的、自我折磨的。劳动变成商品,就有了可以被资本家随意定价的基础。在工厂里的生产关系使得工人之间的关系从紧密连接变得疏离,工厂里的人们只是为了工作的目的而在一起工作,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连接。
异化教育说:天哪,这简直就是我!
学习成果即成绩与学生被教育体制进行了异化:在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雇佣奴隶的学校里,学生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学习,所得到的学习成果,成绩,或许在学生考到全省第一的时候会扬名万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却只是作为学校升学率等数据的一部分而已。不仅学生创造的学习成果被学校利用,学生本身也作为商品在货架上售出,售出为无产者,少部分成为资产者,但总归是为资产阶级持续地创造着血淋淋的价值。学生在成为学生前,其首先是一个人!且不说对于学生的未来即无产者将会被剥夺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并使之成为外在的东西,体会不到人的主体性,就是在学校中,学生——人,却只是被作为一个“学生”,一个唯一的使命就是学习的学生来对待,学生的本质又何去何从了呢?在学校里的生产关系使得学生之间的关系从紧密连接变得疏离,学校里的人们只是为了学习的目的而在一起学习,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连接。
学校中学生所遭到的无情的异化,与社会中工人所遭到的异化岂有多大的区别呢!
反对物化,首先就是要回归人。回归人,首先就是要破除资本主义秩序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就是要发扬作为人的个性。
无数的学生在学校中,被灌输着为了自己而努力奋斗的思想。果真是为了自己吗?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学习是为了自己,不学习就活不下去,仿佛学生从生来就是学生,只有作为学生的身份,没有作为人的身份,只要得到升学,考到大学,好大学那就是最大的成功,过程方式什么的是一概不予过问的。资本主义对人的不同需求所导致的对人的分级,标签化在这种浓郁的反动氛围中更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有人或许会讽刺学生说,你不是反对补课吗,那你不去就是了,这句话宛如对一个工人说,你不是反对加班吗,那你不去就是了。将人束缚在现状中的,在职场上源自产业后备军,更深层地来源于……,在学校中则源自家庭,学校的压力,还有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在当今祖国社会生存的难易程度。认为学生,或者说工人,可以单纯地通过不去取得自己的利益,是荒谬可笑,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说法。认为学生批评学校,自己又考不到多好,是一种气急败坏,是一种无能狂怒的想法更是可笑。在教学资源的分配上,学校极力将普通班和实验班分离开来,而在对学生的压榨上,对于实验班和普通班倒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视同仁,时不时实验班还要受到更多一点的“宠爱”。雇佣劳动是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互相竞争之上的,那学校又是什么样的呢?普通班的同学们指着实验班的同学们说,看呐,那就是实验班,嘴上说着不想补课不想学习,还是考那么高,真虚伪。实验班则被灌输着,普通班就是炮灰,毫无意义,实验班才是出成绩的真正的培养着的学生。学校就这样致力于分化实验班和普通班,一方面为资源的偏向张本,一方面也是为防止普通班实验班“串通一气”,图谋不轨。
直到现在仍有许多普通班的同学,嘲讽甚至敌视地看待实验班的同学,将其不是视为同学和朋友,而是视为敌人,似乎因为占用更多的资源,实验班就是学校一方的人了,受的压迫那就不是压迫而是奖励了,就这样主动迎合学校对学生的分化。学生们互相敌视着,互相竞争着,无可奈何地被内卷大潮裹挟着。学校笑呵呵地看着学生们你追我赶,成绩考出来,校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于是增加上课时间学习时间就能增加成绩的观点愈发根深蒂固了,学生的积极性对成绩的影响被彻底忽视了,学生成为了为了学校和“自己”生产成绩的工具,的机器。而机器是没有资格索要休息的。机器只要浸泡在工厂为自己编织的“为自己好”的美梦中渐渐沉沦,一心一意地做好机器,啊不,是学生的“本分”,为学校生产金钱来源,啊不,升学率就可以了,这就是学生的使命,多么无上光荣啊!多么光明无暇啊!
让学生的情感鲜活起来,让学生的个性张扬起来! 学生们在反动的思想灌输中,在灰色的规训下,只能渐渐走向沉沦,渐渐走向麻木。而麻木
“……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完美地“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与悠闲”。
角色外溢
在学校这一制度化的场域中,未成年人被指派了学生的角色,然而在此之后,学生这一角色就成为了未成年人最为显著的角色,“甚至是唯一的角色”。未成年人在学校作为学生而活动,在校外仍然被要求作为学生来活动着。这样,未成年人在学校做学生,在家里做学生,在哪里都是做学生,学生这一本应是人的众多角色之一的角色,从学校边界几乎外溢到了未成年人活动的所有时空之中。这就造成了未成年人被学生角色没完没了地规范着自己的行为,自己作为人,作为其他角色的机会被强制性地淡忘了。
不仅学生自己被疯狂克扣的假期、繁重的课业导致了自我意识上对学生角色的固化,成年人主观上也是如此。有多少家长在家里不是将子女作为一个应“恪尽职守”的学生来看待的呢?有多少老师在校外遇到未成年人,不是用看待学生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呢?这种对未成年人的精神上的束缚,将会严重禁锢未成年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表达。他们总是被看作是一个学生而已。
“不过人们不是总是这么说吗?对比自己年轻的人?他们说,哦,有一天你就不会再这么想了,你等着瞧好了。就像你没有权利拥有任何严肃的感情似的,就像你没有能力这样做似的。”
未成年人不仅仅有学生这一个角色,未成年人同样作为人,同样有着拥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和严肃的感情的权利。他们有权这样,并且必须这样。非如此不成其为独立完整的人。
社会固化了学生的角色,资产阶级的市场赋予了这些原材料们“厚的”规范期待,从而必然造成学生的负担之深重。想要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做“好学生”,做“好材料”,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更加之众多同龄人的相互竞争,这样需求方统一一致,供给方相互竞争,结果自然是内卷没有赢家,而资产阶级的腰包永远是一天比一天鼓起来。
成年人可以在脱离了工作的时空后卸下角色的负担,而未成年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从精神压力上来说,未成年人并不比成年人轻松。然而比烂没有意义,角色“说到底只是人的功能性的存在方式”,“人毕竟不同于角色”。就像欧文·戈夫曼认识到了角色对人的非凡意义,但也同时明了角色依附、角色固化对人的压制性、窒息性危害。绝不能忽视角色距离的重要性,即人在扮演一个角色时,应该通过特定的行为与该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
将本应多维、丰富的未成年人简化为学生这一维,对做学生做的成功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对于更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则是莫大的伤害。
对于这些未成年人来说,固化在他们身上的“角色之茧”将他们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无法看到一丝光亮。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破除对于未定型的具有多种发展可能性的未成年人的桎梏。未成年人应当尝试多种角色,尝试不同的功能,而非固化于单一的死板的角色,如果在学生这一角色扮演上失败,不至于因此从此落入深渊,而是可以从别的角色中重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多重角色会使人获得潜能实现感,在多种角色的尝试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否定异化对学生的人的本质的否定,从另一个角度上实现对人的复归。
学生角色显著必然导致未成年人的其他的角色受到压制。同样的,这种对于其他角色的压制对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要求也存在着限制的影响。未成年人在家中固化了学生的角色,继而无法发挥作为子女的角色的功能,家长也无法以对待子女的方式对待未成年人,从而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再被撕扯,未成年人从而持久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甚至就此沉沦。迫于家庭的期望与压力崩溃自杀的例子数也数不清。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的未成年人,用他们的身躯砸到地面上的沉闷响声,一下下地为我们敲响警钟。
与学生角色的外溢相伴随的是学校的外溢。 学校与家庭本来是各有边界的功能与伦理实体,如今学校将学生安插在家庭之中,家庭边界对学校来说形同虚设。有人说,“学生通过书包将学校背回了家里”,事实上,学生本身与他们融为一体的学生角色就已经将学校带回了家里。家庭因而变成了学校的衍生物或派出机构。也就是说,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家庭的支配与控制。
学校的伴随性外溢不仅包括家庭,还包括社区乃至社会。不难理解学区这一现象了。学校对家庭的控制,逐渐地扩展成了对社区的控制。这也就是学区化地区价值飞速抬升,乡村等教学资源匮乏的地区价值一再降低的原因之一。学校的外溢也是社会性的。不难理解校外教育机构,“影子教育”的兴盛。学校由于外溢而无处不在了。与学生角色的外溢相伴随的除了学校的外溢,还有教师角色的外溢。教师也被制度化的社会角色所不断规范着,固化着。教师在家里,在休假时也和学生一样无法获得全身心的休息,而是受制于自己固化的角色,无法与工作脱离。
只有打破了私有制,才能够打破资产阶级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社会的一切成员的强制性要求即禁锢,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教育选拔
人们向来呼唤一个公平的选拔制度,可是什么是公平的选拔制度呢?怎么样才能是公平的呢?有些人认为,对于被选拔者来说,付出的越多,从而获得的机会就应当更多,这种基于被选拔者努力程度的选拔,是比较能使人接受和信服的。可是有另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不以被选拔者的能力作为标准,任人唯贤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下,所谓的公平选拔到底是服务于谁的?
将被选拔者作为主体,重视被选拔者的付出与努力的过程,实现多劳多得,这是服务于被选拔者的公平。
将被选拔者作为客体,重视选拔者的利润最大化,将被选拔者视作货架上的商品,只根据一个个的标签考察商品的最终的性能,选拔最符合选拔者需要的人,这是服务于选拔者的公平。
于是又有一些人探出头来,高呼调和,融合个人努力程度与个人能力评价综合作为选拔标准,似乎是实现了“公平”的选拔制度。果真吗?
在私有制的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真正公平的选拔制度即基于个人努力程度作为选拔标准的制度的。在成绩现实化为学习的结果并且学生物化为原材料和商品的过程中,学生个人的活动,学习的过程是不会被选拔者加以考虑的,他们只是以成绩作为最终的标签,按照资产阶级与市场的愿望进行分拣与发货。在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不平等的基础上,还存在着私有制所必然导致的个人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环境的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的前提下构建起来的以成绩作为普适标准的选拔制度,事实上仅仅服务于选拔者即资产阶级,仅仅以选拔者的目的即资本的积累为转移,仅仅与选拔者的利益为标尺的这种选拔制度,当然不可能是真正公平的。这种选拔制度,只是为资产阶级选拔合格的雇佣奴隶罢了。
教育是为了什么呢?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不就是为资本主义培养奴仆的同时,再生产社会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吗?作为将普罗大众与少数人分化开来的选拔制度,不正是这项工作的得力工具之一吗?为什么有人在害怕让所有人都能接受到高等教育?为什么有人在害怕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归根结底不就是资产阶级稳住统治宝座的诸多手段之一吗?那么,要想打破旧学校对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要想摆脱旧教育下学生遭受的物化与异化,要想实现人的平等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难道除了打破这一切的根源即私有制,难道除了阶级斗争,还有别的路子可走吗?
“要为国家选拔人才。”国家?谁的国家?是人民群众的国家吗?是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吗? 为资产阶级当走狗,就是当人民的刽子手。为什么只能选拔一部分人做人才,不能人人都做人才吗?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让每个人获得全面的发展,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可以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人,真正具有当家做主的能力,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有不好,那就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老爷们相当不好。他们会把嘴都气歪的。因为在人人全面发展,人人当家做主的社会中,靠产业后备军维系与加固的锁链将再也禁锢不住无产者;在人人摆脱了庸俗的思想的强制性灌输的社会中,老爷们拼命隐蔽的剥削与压迫将在众目睽睽下无处遁形。
“高等教育是给有能力的人上的。”果真如此吗?北京、上海的老爷们的少爷千金们,果然是全靠了学力升入高校的吗?河南很大,大到有上百万高考考生;河南又很小,小到装不下一座大学城。果真是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考生中没有能力的人多吗?所谓的能力,是否也要包括经济能力、地区教学资源乃至于家庭的社会权力关系在内呢?私有制下出于分化人民群众而导致的教学资源的分配不均,在单一学校内尚且如此明显(实验班与普通班),在地区之间则更是一目了然了。少爷千金们可以通过高尔夫入学一众985、211和双一流高校,以这种绝大多数人平常根本不会接触到的东西作为高等教育的通行证,怎么,难道高尔夫也是所谓能力的一部分吗?有人叫嚣着脱不下来的长衫,鼓动过剩的大学生下放工厂单位,殊不知有多少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连这件脱不下来的长衫都穿不上呢?他们果真是没有能力吗?
“不是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还达不到,是生产力还不够。”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就是出自于对于历史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唯科学主义理解。社会规律作为规律,在客观性,必然性,可重复性,普遍性等方面与自然规律是没有区别,但是如果将社会规律简单地与自然规律等同,“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只能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语)。社会规律的承担者是人,没有人就没有社会规律。我们考察每一个社会现象,如果只从单一的经济因素出发,忽略了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就会走向历史观上的机械决定论与宿命论,得不出真正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结论来。
不可否认的是,选拔制度之废除,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生活高度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以实现。但是在此之前,至少公平的选拔,而且是以人的努力程度为标准的真正公平的选拔,是可以在生产资料已然收归社会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的。在那里,人人自由而平等,不再受任何虚伪的庸俗的思想的浸泡,个人能力的发展,将完全取决于个人努力的程度,而非金钱或权力,或社会地位又或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并不养懒汉,社会主义养的是自主的独立的创造性的人。 社会主义打破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受的禁锢,给他指明解放自身的道路。 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将会大大弥补个人之间生理上的环境上的不平等,并且在此之前,经济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已经被公有制所消除了。因此,社会主义的选拔将会是建立在本身公平的基础上的公平选拔,对经济、身处的环境、发展条件等一切外在因素的不平等的消除,将会是这个公平选拔制度之所以平等的大前提。在那里,学生不再是为了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需要而学习,而是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为了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学习。应试教育与附庸其上的填鸭式教学,将会成为无用的垃圾,它们甚至没有资格“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而是直接被解放了的人民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教育应当是面向人民的教育,应当是服务于人民的教育。 以培养雇佣奴隶为目的的吃人的资产阶级旧教育已经吃掉了太多的人了,它的累累罪行。它对人民的伤害,已经从各地无数跳楼学生的血泊中清晰地映照出来了。旧教育对于人民的分化,已经从北京四中舞会迷乱的灯光中,从学生高尔夫大赛的招牌里照射出来了。旧教育再不能存在下去了。一种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首先意味着它从现实的人的发展形式变为了人的桎梏,变成人自主活动的桎梏。教育制度也是如此。而只有变革生产关系,变革教育制度,才能够带来生产力的解放,同样才能够带来人的解放,带来人的自由的推进。
他们如何做?
中国教育最根本的出发点,无外乎在于使劳动者的子女在成为合格的雇佣奴隶的同时,磨灭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从而确保自身的发展与存续。这主要是通过如下一些手段实现的:
歪曲历史。 比历史虚无主义更反动的莫过于历史修正主义。为了对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认识进行歪曲,中共除了通过大量阉割历史事实外,还持续进行着无耻的所谓官方的反动定论。前者在删减、“规范”历史、政治等教科书的同时与其他信息管控手段联合行动,使人民群众得不到对于历史的全面认识,即使半信半疑,又苦于找不到更全面的信息,结果只好接受官方得出的有利于维系中共统治的历史解释,被迫选择性地接受那些有利于中共塑造其虚假的光辉形象的历史事实。不管其正确与否,不管其全面与否,在中国人从小就从父母长辈那里养成的对学校的无限信任与服从的意识的指导下,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认识就这么被改写成了中共的谎言。由于缺乏了对历史的正确全面的认识,人民群众自然难以产生对当今资本主义政权的反思,又加之中共庞大的宣传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无数御用文人摇动起笔杆,那么中共自古正确至今亦然的认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即使见证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但是转念一想,之前也没见有什么好的呀?好吧!于是也就只是摇头默叹中共教给自己的自我安慰口诀:“还是不够努力”而作罢。将劳动者彻底变为无害的羔羊,甚至切断其头脑中反思意识的来源,这就是中共历史等学科的教育的目的与现实。
树立刻板的规范意识。 高中阶段的选科中,很少会有人是为了学习政治而选择政治,如果不是为了拿分或是无奈之举,没有人会去学习那些写满了看一眼就知道是故意在恶心人的教条词句。即使选择了,在一个不选政治或历史的学生捧着一本相关的书籍阅读都会被质疑其选科的环境中,我们又能奢求选择政治的同学们脱离那充斥着鹿克思主义反动思想的教科书多远呢?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似乎被选择的科目打上了难以摆脱的烙印,标签,似乎选政治的就只能天天背那些恼人的废话,似乎选历史的拿着本哪怕是政治或是社会学相关的书籍看都要被问一句“你不是选历史的吗?”连学生们从这两门本应是生动的学科中学到的知识也被标签化了,似乎选政治的同学不会大谈公文体的废话,不会破案量刑就是渎职,似乎选历史的同学不准时背出个什么时代或是什么文件出来就是对不起选的学科。历史和政治的情况十分类似,无论是书上的内容,还是考试中体现出的要求,无不体现着机械与束缚。历史考试中表面再开放的论述题,背后也总是统一的死板的格式与论调,这样的题目巩固的是学生对于歪曲了的历史的认识,同时也不断地磨灭着学生多角度独立反思历史现象的能力;巩固的是中共在学生心目中伟大而又正确的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形象,磨灭的是学生质疑与批判的能力甚至愿望。
强制性的双重思想。 一面是语文老师在《种树郭橐驼传》中热情地歌颂“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一面又在作文中严格要求着那少得可怜的“健康向上”的充满着奋斗的鬼话的立意,要求着那令人作呕的文绉绉的语调;一面是学校大放着素质教育的厥词,一面又疯狂地压缩着假期,延长着课时;一面是学生们目睹着大城市的少爷千金们优哉游哉的学校生活,一面又起早贪黑,过着仅仅充斥着内卷的生活。这些都是学生们看在眼中的,但是从小养成的对学校的服从,还有对身边其他学生在无形中建构起的服从学校的秩序的服从,以及周围势不可挡的内卷大潮,毫不留情地将愤慨的他们淹没,磨去锋芒,留下泡得温温柔柔的洁白羔羊。 他们愤怒,他们悲伤,但是这种再自然不过的人的感情就这么被无力改变的现实扼杀了!他们除了欺骗自己,自我安慰还有什么法子呢?他们除了要么投身内卷大潮,要么彻底躺平,要么就此一跃而下之外,还有别的路子好走吗?是要怎样的绝望才会将一个个活生生的青年逼上生命中最后的天台啊!是要多么残酷无情的现实逼着他们只能靠双重思想带来的短暂慰藉聊以度日啊!
成绩挂帅的评价体系。 这首先包括着对成绩较差的学生的规训。不同成绩的同学们在讨论问题,特别是历史政治相关问题的时候,每个人的头上似乎立刻就显示出了各自的成绩,不选择此科目的同学不用说,那是纯纯凑乐子来的,大家根本不会把他们的见解当真。而有的人的头上顶着全市几百名,有的是几十名,好像这种人所发出的见解,就自动地比别人的见解多了一层成绩加持的圣光,差生们看见这轮圣光,岂敢违抗这种以成绩决定说话分量的秩序?大多数时间是只得顺从的。越是在这种教育中取得更高的成绩,就越代表着对这种教育的认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成绩就代表了一个学生在这种评价体系中的话语权,假如他考到了第一,那还了得,他岂不是句句是真理!相应地,官方那更加权威的话语岂不更是真理中的真理! 除了成绩在这种体系下自动获得的权力外,成绩挂帅的评价体系还导致了学生学习的目的被单一地概括为成绩,似乎只要成绩考的高就是无上的胜利,并在无视家庭条件、地区教学资源和社会关系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后,强制性地在不平等上推行看似平等的评价体系,甚至就连这样中袖也要为少爷千金大开方便之门,在这一点上想必河南、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不会有丝毫的疑惑。中修假惺惺地推行的艺术特长选拔中,坐拥更多资源的富家豪门的优势是不消多说的,普通家庭甚至要牺牲无数财力与时间以及学生本人的意愿来追求从特长方面与起点便已高不可攀的富家子弟竞争,更不用说什么高尔夫那种普通人连碰都没机会碰的贵族运动了。中修的评价体系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学生在违心的内卷中丧失的无数的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与富家子弟们在逍遥的环境中所获得的相比起来,就拉开了用以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壕沟,前者无数的努力与付出,最终也只不过是成为这名劳动力的一部分为资产阶级创造价值罢了。
扭曲价值观的培养。 成绩挂帅的评价体系引出的无休止的内卷中,同学们本应美好的互助关系被无情的竞争所泯灭了,在这种环境长达三年或六年的浸泡下,未成年人对于竞争与内卷已经是司空见惯,以至于到了职场上也能够心安理得地在内卷中你追我赶,在他人为自己编织的美梦中迷失了自我。无尽的上课,繁重的作业,周考,深夜的晚自习,无不在刷新着学生对以后工作待遇的承受下限,无不在预演着生产场所的机械劳动,分工,交换与分配,血淋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在这种不自觉的演习中得到了这个社会的未来的确证。 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每天六点四十开始晨读,十点放学的学生不对着996大叫福报呢?毕竟996每周是放一天假的,而我们亲爱的高中可是两周才能放不到一天啊!对于自由的空闲时间的奢望就在高中被彻底消灭了,996的剥削制度不仅在学生的心中被合理化,甚至还福音化了。拜金主义在学生的头脑中生根发芽了,顽固的小资产阶级心态在学生的心中潜滋暗长了。人身为人的价值观就这样被扭曲并在漫长的压迫中固化了。这是直指每一个人心脏的利剑。人的心就此被改造为奴隶的心,物品的心,机器的心了。这是杀人。
难免有人化身看破红尘的教师爷或现代的马尔萨斯,复读起什么中国人的本性和人口理论来,什么“14亿人如何治理全世界没有人知道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这种陈腔滥调。这些可笑的辩护士们的吠叫,中国的学生和工人听得已经够多了。他们明确地知道:中共共产党统治集团、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正是中国共产党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本质,决定了他们是如此地害怕人民群众对于自身的处境有哪怕丝毫的反思,以至于他们厚颜无耻地大肆阉割着历史,歪曲着群众的认识,又通过教条化机械化的背诵使人民对政治产生排斥感,并利用标准化的刻板印象的加深疏远着人民群众与政治之间的距离,把政治变成少数人的政治,变成寡头的政治,与此同时又大谈致富经成功路,使人民的自主思维被压抑,沦为温顺待宰的羔羊;
正是中共浓厚的官僚主义作风决定了他们与人民群众的极度隔阂。 形式主义与贪污腐败盛行的官僚评价体系不断向下腐化着学校的评价体系,从而进一步扭曲着学生评价体系。无数的空话与假话,自上而下渗透着全中国的方方面面。瞒上欺下的中共干部那害人的形式主义,将人民群众变成自己的政绩中或真实或虚假,总之是可有可无的数据,并疯狂地动用一切手段来镇压着一切不利于自己乌纱帽的忤逆行径。人民群众在中特的手下只是被作为不论死活的奴隶般对待;
正是这些权贵和官僚所捍卫、依靠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将未成年人培养为可堪使役的雇佣奴隶的骇人要求,这不仅包括强迫学生学习无效无用或违背本意的知识,还包括通过对压迫剥削的合理化辩护打消奴隶们反抗的可能,不断加固着束缚着劳动人民子女乃至整个无产阶级全身的锁链,妄图使人民不得翻身解放。正是中共复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一切拉回市场的脚下,迫使一切为了市场和利润而服务。 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妄图通过对人民群众子女的分化挑动内卷与对立,在一批批同样处于被压迫地位之中的无产者的相互斗争中攫取沾满鲜血的暴利。
我们如何做?
人的意识不是也不会是线性上升的,就如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会线性上升一样。以脱产为铁证强加罪名给进步学生,无视他们的诉求和力量,是任何先锋队都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抖擞起精神为“进入居民的一切阶层中去”准备,为动员起一切反秩序的力量准备,为从现在开始着手抵抗中国进步左翼力量的原子化状态准备,为提早哪怕一天具备给群众提供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准备。
“现在就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