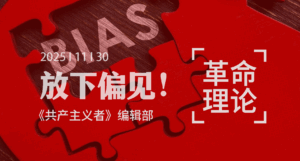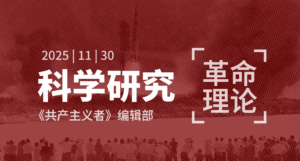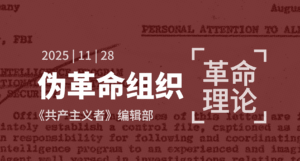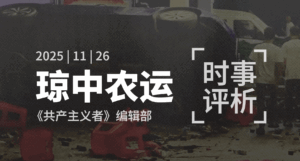《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从原始人围坐在篝火旁第一次奏响骨质乐器开始,文化就没有任何一秒脱离了人类的视野。采集、渔猎或是农耕;搬砖、编程或是写作,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生活中通过动作、文字、声音乃至其活动本身等表达着作为个人活动的感想、思考或评论。文化问题贯穿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发展过程的优秀写照。清晰地阐述文化问题对于我们认知历史、指导未来都有着不小的意义。
什么是文化?
文化一词,就其起源而言,最初由西塞罗阐释为“灵魂的培养”,而后在不同语境下存在着诸如经验积累、人文教化和公共潜意识的外显等多种解释;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则是通过不同媒介表达的一般的社会思想及其所蕴含和得以展现的特殊的个人思想。然而,文化的意义与其一般所表现出的直接现象相反,其决不是脱离了物质而凭空出现在人脑中的臆想。相反,人的任何思想都必须以他所接触的一切外部物质环境为基础——一个以社会性为其基本性质的人,不能不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所处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在生产中占据的不同地位,发生的不同关系中汲取产出思想活动或文化创作的原料。因而文化就其本质的一般性而言,必须是基于一种普遍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认知方式——文化是物质的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中广泛的反应。
作为封建主、古典帝国官僚和资产阶级文化创作者存在的艺术家们都曾经创造出属于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的文化,而科学社会主义者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劳动者在文化创造中的主要地位将超出之前统治阶级文化狭隘的范畴。无论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之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政权之中,无产者的文化创作都不仅意味着占据生产关系最主要物质生产地位的群体将会产出最能够反应该物质基础的文化产品,更能够代表其同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无产者的文化产品必然从不同视角包含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动态的斗争过程,并将作为人类历史进程本源的阶级斗争辩证地塑造为一个整体。再也不会有人在研究古代庄园、城堡、壁画和宫殿的时候忽略附属于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被资产阶级史学家定性为“不值得学习”的文化印记——属于被剥削者与劳动者的文化符号将被给予同一切剥削者文化相等的关注,社会主义史学将以阶级斗争的视角重塑我们认识人类社会迄今以来一切历史与文化的方法。
文化与政治
在所有产生不同文化的物质基础之上,阶级社会的文化将必然辩证地包含阶级斗争这一基本进程。由此,所谓社会的文化必然会存在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的意识形态——正如社会生产中必然会存在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那样。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创造维护自身再生产条件的自然倾向,并自然地导致上层建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压制其他意识形态与文化体系,进而对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关系产生反作用力。
这一过程既包含了我们所熟知的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又包含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前者不仅意味着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劳动力对现存秩序规范的服从,即工人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服从与全社会作为集体为剥削者和食利者集团产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这种能力被国家机器的综合运用保障。因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即社会文化,在其塑造和展现的过程中不能不具备起码的政治性——这似乎会导致一种结论,那就是既然由于纯粹的文化,“为艺术的艺术”的不存在,那么任何阶级想要进行统治或至少是筹备进行统治,就必须抢占文化阵地,就必须自觉地在社会文化中推行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有文化的军队”,使得文艺不仅是要变成革命机器的一部分,而且是要变成政权的一部分,就像曾在中国和苏联所发生的那样。
基于类似结论而产生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重要聚焦点。在阶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两类现实主义:一类是肯定的现实主义,一类是否定的现实主义,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是新旧阶级斗争关系中的一体两面——当一个阶级尝试通过各种方法取得或巩固统治地位时,它不能不懈怠了对它构建或构想的理想秩序进行的赞颂;同样,被迫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不能不为了追求同样的目的而结合其被统治阶级之地位所带来的现实发展出批评或否定现存秩序的现实主义。举例来说,前现代君主制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控制力有限的治理结构会不遗余力地歌颂皇帝、国王、贵族与骑士,号召全社会的节制与禁欲,而兴起的资产阶级却会主张回归人的现世生活,为导向萌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消费或享乐主义张本;建立了稳固统治的资产阶级会积极宣传作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家庭观念与维护社会生产环境稳定、国内市场统一的“爱国主义”,而不屈的无产阶级将会一分钟也不停地从受尽压迫剥削的生活得到教育并将对自身苦难的感知发展为各种自发的工人阶级艺术,如早期的街头涂鸦与爵士乐。
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们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他们被卢那察尔斯基称作战斗者和建设者:他们自觉地批判了有产阶级静止的现实主义,从自身左派知识分子的角度去抨击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所蒙蔽的黑暗现实的同时也揭穿了反动分子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怀好意的发自“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攻击。他们坚决撕下有产阶级温情脉脉、反动的现实主义,把旧社会最深的黑暗和新社会最亮的光芒同时表现出来。的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一方面重视现实,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成果;但是他们一方面又展望未来,希冀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从现实的确切趋向以发展的观点描绘可能达成的未来。当下现实的斗争怎么能够不在共产主义的手里与未来的物质基础结合起来呢?接受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浪漫主义地展望未来,注重当下、脚踏实地但比任何人都重视通过艺术团结进步力量和更坚定地迈向未来——因为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决不是怯懦地逃入空想世界,却是反映现实——发展中的、未来的真正的现实——的重要方法。
诚然,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按照无产阶级的意愿改造世界的意图,无论是在政治行动上还是文化创作上皆然,社会主义政权的文化机构也当然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各种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的文化产出自然都要自发地服务无产阶级专政,满足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完善经济基础、推进政治建设的诉求,然而,尽管这样的目标十分美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对于实现这样美好愿景的方法论却出现了严重的误会。卢那察尔斯基及此后采取社会主义之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和政客,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共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政权的政客都采取了可以概括为“政权对文化的彻底垄断”策略——这就是说,他们要借助文化的政治性扩展行政官僚的权力,而非无产阶级民主与劳动者自由表达的权利,是要让文化“服从属于国家机器的政治任务 ”,而却忘记了此时的国家机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残留,还远远无法代表尚无自由、民主地表达自身思想的广大无产阶级!借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武器,许多仍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时期甜美的国家机器集权呼唤、因新政权缺乏人才而留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旧官僚、旧权威肆意妄为地打压一切无产者争取自由的文化创作的权利,攻击一切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先进潮流——苏俄文艺“白银时代”被粗暴地结束、革命样板戏被严格约束成政治词句的堆砌正是铁证——作为合理的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基础诉求的呼应遭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用和扭曲,成为了国家官僚审查和打压自由创作权的工具。这样的悲剧不能不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又一血淋淋的教训。科学社会主义者绝不能够在革命之后相信国家机器“自我改造”的自觉,也绝不能够依赖某些专家和知识分子从脑海中凭空臆想的所谓“革命策略”——只要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残留仍存在一天,无产阶级就必须被动员起来拿起笔杆,通过最广泛的自由创作权,在上层建筑中建设与捍卫业已焕然一新的物质基础。
技术与文化
技术的发展过程同样无法摆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影响,并同时对文化创作与传播的链条施加巨大的反作用因素。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为文化创作提供了载体,航海技术的突破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但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无时无刻通过其反动政策的方方面面提醒我们一个充满人民血泪的事实:无论是在封建等级社会获取起码教育的困难,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产出最适合资产阶级所需的劳动力而进行的教育资源倾斜,都揭示统治阶级仅仅根据自身利益而自觉封锁大众接触完善的教育、防止全民掌握技术的丑恶嘴脸——这是为了捍卫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生产过剩和所谓“廉价劳动力后备军”而服务的。资本家们制造最先进的机器,却发动最残暴的下岗浪潮;剥削阶级提出最“素质”的教育体系,却只供食利者的子弟们享用;金融巨鳄掌握着全世界最高效的媒体平台,却散布着最为低智的奶头乐麻痹劳动者的思想——与之相对的,由全世界工人发动、长期以来坚守社区的开源运动却代表一场由无产者自发产生、反对资本通过“知识产权”定价、垄断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智慧财富、以不为资本折腰的全民技术为理想的解放性运动——这场运动产生了世界大量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使用的、无法被资本家监控的各类安全互联网平台与操作系统,以工人阶级的线上社区为基础在数十年的连贯时间内创造了让垄断资本家惊慌失措的规模扩张,给予无数人民使用最新科技成果自由地表达自我的能力。技术要为全人类服务,也只有在为全人类服务的过程中,技术才能够不仅仅是作为经济基础的一员,而且是帮助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者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影响上层建筑的的道路。
未来会怎样?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借助技术提高自我、把握自己,无论答案如何,至少解题的方法能够由他们来亲自书写了。
怎么办?
阶级社会的文化因其要求维持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所形成的上层建筑必然追求一种蒙昧或半蒙昧的文化状态,其目的在于抑制人们表达自己的意志的能力,通过把人的活动异化、客体化而消灭每个受剥削压迫者的的主体性,让他们彻底成为可供采撷的劳动力容器而非活生生的、完整的人,让每一个劳动者当一辈子奴隶,当一辈子工具。相反,社会主义以及其所导向的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恰恰是由全面发展的、认识并占有全面的本质的一个个“完整的人类”构成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的经济基础所要求的上层建筑必然是在一切方面坚决贯彻自由与解放的的上层建筑,它不能不把最彻底的表达权还给自由人民的联合体,进而摒弃官僚集团无耻的文化发明以及通过文化领域对无产者的异化。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文化产物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为了消灭包括自身在内的旧社会残留要素而存在。真正脱离了政治和阶级的文化有没有可能存在?当然可能,但只有因阶级的消亡而导致阶级文化消灭时才存在——但是这决不是官僚集团像他们口中念着未来不知猴年马月的国家消亡的真经却干着官僚化社会主义政权的下流勾当一样无耻僭越一切文化创作的借口。让凯撒的归凯撒,缪斯的归缪斯吧!健康的社会主义文化从其诞生到完成其阶级意义上的历史使命而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消亡的消亡,自始至终是依赖于健康的土壤,即由劳动的无产阶级民主掌握的计划经济之磐石,而决不是官僚与学究摇摇笔杆子就能够指导创造的。
那么革命的新政权到底该如何对待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残余?文化领域的对立由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剥削关系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残余与新生的、充满工人阶级秩序的计划经济之间物质基础最尖锐的对立矛盾而产生,这种情况并不会在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取得进展前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某些组织的意志为转移。恰恰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不得不在经济基础中保留的,以按劳分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存持续影响着上层建筑,而这就要求任何革命者都决不能懈怠党最初始和最根本的任务和基础,那就是在充分的工人民主的地基上坚决贯彻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通过推动物质基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从根源上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铺就更完善的道路。诚然,人的意识的发展并不是线性上升的过程,维护社会主义政权也不能仅仅依靠人民的自发性,但是也绝不能仰仗官僚的包办与僭越——无论是革命党还是社会主义政权的管理机构与无产阶级自身都无法独自完成维护社会主义改造与过渡的政治任务。
因此,虽然作为先锋队的革命党作为无产阶级中最激进分子的代表,肩负着自觉干预历史过程,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上去的任务,但绝不能把这个任务归类为纯粹组织性的问题,而抛弃了对无产阶级意识的教育、抛弃了通过引入无产阶级民主而对旧国家机器进行的彻底重塑。革命的言论自由将不是自由派所幻想的完全自由放任,也决不应是某些知识分子和御用笔杆子“我也是十四亿分之一,怎么我就没有感受到任何压迫”的言论自由。革命的党在夺取政权后必须要做的恰恰是与剥削阶级的政党完全相反的事情——进行最全面最深入的教育,让每个劳动者掌握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具备艺术表达与政治批判的能力。只有这样,革命者才能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地实现在当时缺乏物质与政治基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未能实现的、在充分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劳动者之间最真切的言论自由。把文化还给得到了充分全面发展的人民——这就是共产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至高回答。